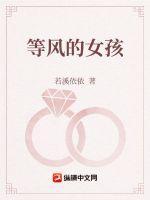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同宿(第3页)
同宿(第3页)
她后来仔细想了想,今日之事有一半是冲着她来的,即使淳于氏并未出面设计陷害,更没有明说,她也一定是乐得促成自己受罚这样的局面的。
当日的一番交白,算是彻底失去了效用。
但陈定雯这个她认为的始作俑者受了比她更重的责罚,她自然高兴。
——她该不该感谢陈定霁呢?
她为什么要感谢他,若是追根溯源,将她和林林困在此地而无处施展报复的,不是陈定霁是谁?
她做梦都想带林林离开这里。
这样想着,庄令涵便也不知不觉行到了东苑内堂,陈定霁的主卧就在前面,她停了下来,轻轻唤了晴方一声。
“秦媪说了,这几日府上都在忙着老太君生病之事,所以这东苑内专门为女君辟的卧房,还没有空闲收拾出来。”晴方见庄令涵站在原地不动,一想便知道自家女君的疑问,“这几日,女君恐怕都要宿在君侯这里了。”
庄令涵心下一沉,想到了陈定霁那要起来不管不顾的性子,脸上莫名烧了起来。
之前可能他还顾忌着外面,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主卧可是他自己的地盘,她若是和他宿在一处,难保他不会为了风流快活,做出些什么出格的举动。
更何况,她需要单独的空间来完成自己的计划,与陈定霁宿在一处,她便没了这个机会。
“女君?”晴方见她有些迟疑,便试探地问了一句,“我今日也问过秦媪了,君侯一向自己单独就寝,女君这几日,也只是暂时宿在君侯这里,女君不必担心。”
待庄令涵神色如常地入了陈定霁的主卧,看到陈定霁一身中衣中裤斜卧在矮榻上闭目养神时,那些本不该此时回想的记忆,又突然涌了上来。
陈定霁的中衣半开,隐约露出其中皮劲肉实的胸膛,他的身上比脸上手上都要白了好几分,若是不经意瞥见,会以为他也是那流传在无数街头巷尾的风流名士之一,只好附庸风雅,清谈闲坐。
可惜,陈定霁皮相再好终究是假的,他自己亲手杀人或轻飘飘叫人灭口之时,可没有半点名仕君子的恭俭谦和。
不知是不是房中没有放炭盆,庄令涵除下斗篷之后,竟然觉得有些冷。
饶是如此,他衣衫单薄地卧在榻上,也丝毫没有半点不适的神情,甚是悠闲从容。
听到她的脚步声,陈定霁才缓缓睁开了眼,并未其他动作,只幽远地说了一句,“过来。”
这是他第几次这样命令她了?
她不是他麾下的士兵,原本也不需要听他的号令。只是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拿捏着她的把柄。
有时她想,她若是个无情之人多好。
庄令涵深吸了一口气,才挪步到他的矮榻前,他在她几乎抵达的同时翻身坐了起来,用拇指放在她嘴角肿起的地方,但并未用力。
“回府的时候,忙着收拾琤琤去了,都没仔细看看你的伤口。”他难得这样的语气,她受宠若惊。
“不碍事的,”既然那时她已经对他乖顺了,此刻便不能出尔反尔又对他恶语相向,她便只能装出那副懂事的模样,“只是有些红肿而已,过两日便好了。”
“琤琤实在过分,今日母亲下令,打你左右脸各十下。”
陈定霁的拇指却突然用力按了一下,庄令涵痛得“嘶”了一声,想要伸手将他拨去,忍了忍,最终还是停住了。
“很疼?”他却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不是说不碍事吗?怎么我轻轻一按就痛了?”
“按,就痛,”她不想自己戳穿自己的伪装,只能绞尽脑汁争辩,“不按,自然就不痛了。”
陈定霁嗤笑一声,握住她的腕子,让她径直坐在他的腿上。她的织锦缎窄袖与他丝质的中衣相碰,不过方寸之间,她还是闻到了他身上沐浴过的气味,和她从屋外带入的寒夜凉气,竟然也能和谐相融。
“我今日已经教训了琤琤,让秦媪打了她嘴角,左右各二十下。”他的手停在她纤细的腰际,只是触碰,并未有什么不轨之举,“算是替你出气了。”
这些她其实早已听了斛律云绰说起,此时再听,便平静了不少。
庄令涵将手指轻轻放在他握住她纤腰的腕子上,盯着他舒展的下巴,道:“原本是妾做了错事,妾受罚是应该的,受言语侮辱也是应该的。只是可怜了赵太医,还有君侯你的面子,都因为琤琤那几句荒诞之言,白白折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