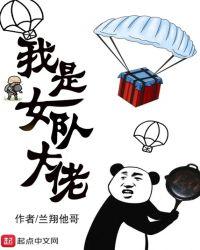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更衣(第3页)
更衣(第3页)
她只是担心袖中藏的药包,若要再去西苑用饭,时辰久了,难免不会露馅。
“无妨,我陪你便是。”
只是这个“陪”字,到底包含了多少暧昧不明的意味,连庄令涵自己也说不清楚。
因为这几日照顾白氏的病,北苑里便给她和赵太医各自辟了间小厢房,供他们休息。今日她其实回去过一次,稍稍沐浴整理了一番,又睡了两个时辰,才起来接替赵太医,继续守在白氏的床前。
给白氏侍奉完了汤药,陈定霁并未多停留片刻,便与庄令涵一并入了那厢房。
晴方从外面关上了房门,庄令涵见他直直看着自己的眼神,原本就惴惴不安的心,忽然有些不知所措。
“君侯,妾要更衣。”这厢房比陈定霁东苑主卧连着的耳房还要小了几分,除了一张床榻外,便只有一张矮几和几把矮凳,连遮挡的屏风都没有。
陈定霁并没有动作,只是看着她略显局促的模样,勾了勾唇角,“夫人的意思是,要我帮你?”
他就站在她面前,晴方关了门,他便跟了她的脚步,一副随时想将她吃干抹净的模样。
“不不不,哪敢劳动君侯大驾,”她连连摇头,他却已经伸了长臂将她锁在了怀里,她的前臂堪堪抵在他结实的胸膛前,她却紧张到期期艾艾,“妾,妾自己来……”
袖笼里还有那个药包,她不能被他发现。
想了想,庄令涵便只能就着这个姿势,扣回了手,解了锁骨那处的盘扣,再去解腰上那处的系带。
他低头,在她裸。出的肩窝上落下了灼热的吻,他的鼻息埋在她圆润的肩头,和他嘶哑的嗓音交错:“枝枝身上的药味好浓。”
她不语,衣袖沿着她光裸的玉臂落到了肘部,她一边解着腰上的系带,一边看了一眼腕子上明显淡了许多的青紫痕迹,道:“君侯,你不想和他们一并用饭了吗?”
又过了一日一夜,他上次在夕香院迫她时留下的那个骇人的痕迹,才终于慢慢消退了。
他不语,她便顺势脱了那袖笼里还藏了药包的外袍,小心裹成一团,扔在了耗不起眼的墙角。
今日天朗气清,脱下外袍之后,她便只剩下里衣了。
陈定霁那双炽热的手却沿着她送上门来的光。裸脊背一路上行,窄袖的袖口卡在她里衣后背的系带上,他却没有再动了。
“枝枝,”他看着她,剑眉微蹙,“为何你对这行医之事如此扑心扑力?既然母亲请来了赵太医,你乖乖退居幕后便是,又何必主动揽了这差事?”
他不懂,她也根本不愿意对他多费口舌。
他不过是恼恨她为了照顾白氏的病,不能和他宿在一处罢了。
“也不知今日云绰见她长姐,会和她倾诉些什么。”她学着他的样子,不回答自己不愿意回答的问题,“若是她为了她长姐伤心难过,料想应该也不会和君侯的弟弟妹妹们一道吃饭吧。”
听见她的答非所问,陈定霁却在她的细腰上狠狠掐了一把,道:“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她吃痛,却拿他毫无办法,只想快点换好衣服去与林林汇合,便低了头,颇有不耐地道,“妾向君侯已经表明了许多次了,妾有自己的志向,可是君侯既然看不上,又为何反反复复问妾?”
他将她下巴抬了起来,默了默,语气中辨不出息怒,“这才熬了一日,你的脸好像小了一圈。”
然后低头看着她里衣之下若隐若现的软雪,声音又哑了一截:“这里,似乎也小了一圈。”
“君侯这是心疼了?”庄令涵笑了出来,不知是在笑他浅薄贪色还是在笑自己的荒诞处境。
她这堪堪露出的雪白肌肤上,还留了许多他昨晚留下的痕迹,陈定霁呼吸一滞,听到她的语带讥讽,本来已经蓄了力的手掌,也不自觉温柔了起来。
“夫人想让我怎么回答?”他又换回了“夫人”这个称呼,“夫人应该也知道我的,即使我嘴上说着心疼,下手,会是另一个结局。”
“时辰不早了,”眼看着二人耽误太久,她实在有些疲累,“妾腹内空空,实在是想吃些东西。”
“我也饿了,”陈定霁却快速接了话,“可是,我只想吃你。”
昨夜的好事进行到一半,被生生打搅了,他的火便一直憋到了今天。如今美人在怀,他又怎么可能真的,只是来“陪”她换件衣裳?
“君侯,”最终,她还是被他打横抱了起来,只用了几步,便被放在了床榻之上,她被他按住,看他单手脱下了自己的外袍,“老太君还病着,主母还在守着,你我却在此,在此……”
“在此如何?”他明知故问。
“白、白日宣。淫,躲着做这不孝之事……”她被他封住了香唇,只漏了之言片语出来,“君侯乃国之栋梁,家中祖母暴病,理应亲侍汤药,当,当为天下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