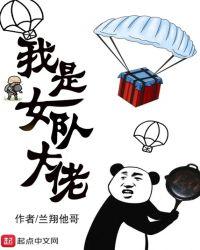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更衣(第2页)
更衣(第2页)
经过了接近一整日的奔波忙碌,此时药房中除了守在她身后的晴方以外,其他人都各自退下,只留她一人守着这堆药材。
她要亲自捡药煎药,不能假手他人,其他下人也不需要留在她身边。
来国公府之前,她便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只是,国公府不比铭柔阁,不能经常让晴方出府为她采买,也怕暗中被人盯上,晴方再行一次重蹈上一世的覆辙。
这也是她一定要亲自经手白氏的汤药一事的原因。既然药房中有现成的药材,她只需要在每次捡药时,趁人不备,偷偷拿一些,积少成多,也够完成她的计划。
比如现在。
烈焰上陶药锅还在咕嘟咕嘟冒泡,煮好了这一碗,今日也便不需要再为白氏多备汤药了。
庄令涵将偷拿的一小把药材用身上的巾帕包好,塞进袖笼之中,刚准备让晴方来掀开锅盖,转身却看见陈定霁立在药房门口,不知目光落在何处。
她莫名有些心虚,但还是要强作淡定,不然,他即使没看见,也会因为她露出的端倪而对她产生怀疑。
既然是个长久之计,任何一步都只能小心翼翼。
“君侯,”她施施然行了礼,手上攥紧了,脸上却保持着浅浅的笑意,“君侯怎么会到这里来?”
晴方低头上来,用打湿的巾帕揭了盖子,又蹲下将火调小了些,便适时地退了下去。
“我刚刚去看过祖母了,祖母虽然还是没有醒,却比早晨我走的时候,面色要红润了许多。”陈定霁却没有如她所料那般进来,也许是这药方实在污秽不堪,他实在不愿踏足。
“老太君这样,是正常的。不出三日,应该能够醒来。”她保持着先前的语气,“君侯,可还有旁的事?”
药房所处偏僻,自然没有卧室之内那么足的炭火。今日虽然比起昨日要暖和一些,但药房内为了保持通风,比寻常的卧房多开了许多小窗。
先前只有她一人在时,为了取暖,她便特意坐在了火炉的周围。眼下在他的直视之下,她忽然受到了一股热意,不知从哪里涌上来的。
“君侯?”可是他不说话,她便不好别的动作。
“过来。”他和她隔了两丈开外的距离,他想看她,便只能开口让她动步子。
可是炉上的药快要煎好了,她若是不顾火,一番心血便只能作废。
所以,庄令涵没有动,反而叫了晴方又进来,将药锅取下,再将滚烫的汤药盛出。
“将这药给祖母送去,母亲在那里,她会亲自侍奉。”陈定霁对端着托盘往外走的晴方说道。
他先前已经去过卧房看了白氏,然后晴方一反常态独自去送药,淳于氏自然会想到,他是来找她了。
虽然她并不奢求淳于氏的信任,但她也不想被淳于氏看低。
“既然君侯来了,为了表示你的孝心,又为何不亲自侍奉?”
室外寒凉,晴方用铜制食盒装了药,再提到北苑白氏的居所去。只剩他们二人,庄令涵便走到陈定霁身前,再福了福身,柔声说道,“这药房本也不是君侯该来的地方。”
“你倒是替我考虑得周全,”陈定霁只伸手,用粗糙的拇指和食指捻了她红润的耳珠,轻轻揉搓,“不怕我在这迫你?”
痛痒难耐,她稍稍躲了躲,想到他以往不管不顾的兽行,竟然不自觉抖了抖。
陈定霁最爱看她那面露惊惶又不得不屈于他淫。威之下的乖顺神情,俯身在她额前轻轻吻了吻,才道:“三郎在西苑摆了几道小菜,请了斛律小姐和你的林林弟弟共进晚饭,五郎和玫玫也在,玫玫担心我这个做二哥的知道会惩罚他们,悄悄命了人来知会一声。”
“三郎?”庄令涵皱着眉头,但一想,便已经估摸出了一二。
那日在长安城门口替斛律云绰解了围、又将自己的马鞭送给她的,应该就是她匆匆见过两次的陈定霖了。
虽然国公府很大,但毕竟同住,斛律云绰又是个爱玩爱闹的性子,难免不会碰巧撞见他。
“按说祖母现在病中,母亲还一直侍奉在侧,他们几个不过来为母亲分忧也就罢了,还要私下相聚。”陈定霁的语气沉了沉,却话锋一转,“这个时辰,夫人应该还没用饭,不如,也和他们一并?”
“君侯,也许不是他们几个不想,是主母不太允许他们几个过来亲自侍奉呢?”庄令涵想起了白日里,他的几个弟妹倒是轮流过来探视过白氏,但淳于氏却没让他们上手,“药快凉了,君侯身为长兄,还是要做好表率。”
“那给祖母侍奉完汤药,夫人与我同去?”他难得用这样的口气询问她。
“既然君侯这样告诉了妾,也必然不是要阻拦他们,”庄令涵自己也想见林林,即使不能单独和他叙话,光是看看也是好的,“只是妾一身蓬头垢面,要见他们,还要单独换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