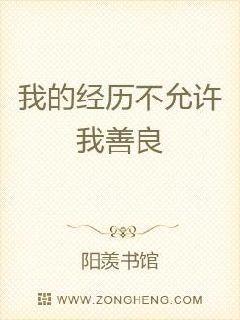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木屋(第3页)
木屋(第3页)
***
卯时初刻,初冬的天色还笼着一层半蓝半黑的薄雾,庄令鸿勉强撑着心神,不让自己闭上早已沉重无比的眼帘。
面前的陌生姑娘似乎中了迷药,此刻还尚在昏睡,根本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自己现在身处敌国,又刚好与敌齐的太后和权相同处延州之地,知道姐姐令涵在这里,他反而更加焦急,想要见到她。
可是这突然出现的姑娘却阻了他的计划,他虽然也并不喜胡人,觉得他们粗鄙野蛮,可这妙龄少女晕倒在他身前,若要他真的完全放任不管,他自诩正人君子,又根本不能做到。
思前想后,他只好把她带到了一处隐蔽的破屋里,幸而一路上并未被人发觉,不然,若是有齐人官兵说他当街强抢良家妇女,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庄令鸿单手撑着下巴,望着面前昏睡的姑娘,眼皮还是越来越重。他一路奔波了快要二十日,人困体乏,甫要他做这空守之事,困意便如六月的暴雨一般,根本阻拦不住。
而在他又一次因为睡着而垂头,被自己脖子上的动作惊醒时,他发现,那姑娘不知什么时候也醒了,正瞪着那双小鹿一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姑娘,你终于醒了……”他自觉应该先开口,打破二人之间略显尴尬的沉默,但那姑娘却曲起双腿,连连后移了好几下,然后才皱着眉头,直直盯着他的脸道:
“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姑娘昨夜在街上乱逛,不小心撞到我了,我正要赔礼道歉,姑娘却晕倒了。”庄令鸿看着她的眉头越皱越深,话语也不自觉越来越慢,“我,我见姑娘晕倒,实在不敢把姑娘独自留在街上,便只能寻了这处,守着姑娘,看看姑娘何时能苏醒过来,好解了这困局。”
那姑娘闻罢,眉头微蹙,狐疑地撅了噘嘴,又不动声色地检查了自己的衣物,才小声说道:“你……你真的除了守着我,没有再对我怎么样吗?”
不知为何,庄令鸿却觉得自己双耳发烧。
昨夜刚刚把她抱进来时,他是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
他见过的胡人不多,胡人女子更是少之又少,这个姑娘虽然比不上自己姐姐的天香国色,但细看之下,却有着另一番异域风貌。
她虽然熟睡,可那双鹿眼却和鸦羽长睫一并恰到好处地覆在她麦色的肌肤上,长睫打出的阴影之下,是她长于草原才会有的浅浅红晕。她的嘴唇虽然无甚血色,却在半张半合间浅浅露出雪白的贝齿,若是她开口说话,又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呢?
但庄令鸿很快便停止了自己的遐思,他是君子,是日后居于庙堂的正人,从小受礼学教化,非礼勿视的道理,是从开蒙起先生便教导他的。
何况,眼前的女子是胡人,又极有可能是鲜卑人。
中原汉地江山,已被胡人入侵了数百年,无数的汉人同胞,都死于胡人的屠刀之下,他每每读史,都忍不住扼腕叹息;如今这齐地,更是由鲜卑人独孤氏所创,胡人与汉人的血海深仇,庄令鸿是不会忘记的。
所以,他只不过使出于对这陌生姑娘的天然同情,才出手相助,对于她这个人,他应当心如止水。
不过犹豫了片刻,庄令鸿便正色,回答了她的疑问:“我是正人君子,自然不会对姑娘如何。倒是姑娘你,身中迷药,你可知道,究竟是何人要害你?”
“迷药?”斛律云绰第一次听闻这个东西,疑惑万分:“迷药是什么?”
“迷药就是……”庄令鸿颇有些无奈,他先前只觉得这姑娘略有点天真,却没想到她竟然不谙世事至此,“迷药,就是会让你昏迷不醒的东西,昨夜你在我身前突然晕倒,想必也是这迷药作祟。”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中了迷药?”斛律云绰又皱了皱眉。
“医学乃是家传,在下不才,也略得几分傍身。”庄令鸿沉声道。
斛律云绰最听不懂这些汉人的文绉绉,想到眼前这个清俊男子守了自己一整晚,又将她身中迷药之事如实告知,应该,也不会是坏人。
何况,他和令涵姐姐长得有五六分的相似,虽然她也知道两人应该并无什么关系,可除了信任,她也对他生出了几分别样的好感。
迷药……迷药这个,若不是彭楚那样的坏人想要对她不轨,恐怕,恐怕是她那姑母做的。
至于为了什么,她暂时想不明白,反正不是好事。
真是这样的话,她便更不能回去了,自己好不容易跑了出来,再这么直接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斛律云绰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反正……你是好人,对不对?”
庄令鸿被这样直白又语焉不详的句子问住了,愣了一下,才道:“姑娘何意,我实在听不明白?”
“我叫斛律云绰,是这延州太守公孙信夫人的侄女,我姑父要逼着我嫁给汉人,我不想嫁,家里便用这迷药对付我。”除了身份有变,其他的遭遇却也不是她胡编的,“如今,我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但我姑父是延州的最高长官,在延州城内一手遮天,我出走了,他们一定会全城搜捕我。”
庄令鸿剑眉动了动,似乎已经猜到了她接下来的话语。
“既然,既然你是好人,能不能帮我到底……”她声音渐细,一面观察着他的反应,“我想出城,只要出了城,我就不会再麻烦你了。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斛律云绰?齐国现在年轻的太后就姓斛律,若是他没有猜错,眼前这个姑娘,恐怕真与齐室有关。
而姐姐令涵,应该也就在那齐国太后和齐相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