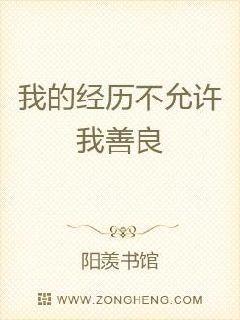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木屋(第2页)
木屋(第2页)
木屋的墙上,是被烛光照耀折射着的深深浅浅的人影,晃了又晃,交织出许多语焉不详的形状。矮桌上,他初入屋时点亮的蜡烛渐渐燃尽,烛泪滴了下来,如此时的庄令涵一般,在数不清的荡漾飘摇里,慢慢地失了根骨。
她累了,累到连避他都没了力气;她的嗓子也哑了,不知从何时起,她就已经忘记了强忍声线。原来这本就活龙鲜健的男人,中了媚。药之后,会是这样一副样子。
在彻底晕过去之前,他还在不知疲倦,她垂下沉重的眼帘,在他背上胡乱抓着的手,也终于落了下去。
清晨,陈定霁先醒了过来。
他从身后抱着她,鼻间是她青丝特有的清甜香气。
怀中的女人还在沉睡,而劳累了一夜的他本该休息,可此刻,却再也睡不着了。
昨夜,他虽然中了媚。药,但他思维清晰,头脑灵活,在他追着她出了太守府的时候,他便已经想明白了斛律太后的计谋。
要下药害他?可以,但他自恃定力过人,即便是别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被送到他面前,他也自信能坐怀不乱,不让对方得逞。
可是,若是用她的身子来为他解毒……
只是想想,他便觉得浑身更加燥热了。
他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露出自己的软肋,还未出太守府,便转身去寻了自己的骏马来。他知道此时的延州城已经落了钥,她没有那么轻易出城,无依无靠,她暂时就只能在街市上游荡。
她走路,他骑马,延州城也不算多么大,他总能找到她。
果然,连他的马都被她吸引。
他不过行了片刻,便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她。
再次把她抱在怀中时,他身上的那团火已经几乎呼之欲出,他强忍着纷乱的心神,带着她出了城,直奔城外山间的密林,只想找一个无人能见到的地方,再好好与她共赴那只属于他们二人的、亲密无间的幽深秘境。
在之后,她便以医者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完成了对他这个病人的解毒疗伤。在无数个夜晚的绮梦终于成真时,他难以控制自己,不断地向她索求。
他知道,从此以后,她便只属于他一个人了。
她是他的。
她逃不掉,谁也不能将她再次夺走。
想到这里,陈定霁再也无法入睡。他又吻了吻怀中佳人那哭得红肿的眼皮,用大手缓缓勾勒她滑腻的曲线,心中原本平息的悸动,忽然又冲上了他的头顶。
这个姿势,他昨晚似乎还没有用过。
“陈定霁,陈文光,你这个薄情寡性的畜生!既夺人之妻,又护她不住,除了发泄你的兽。欲你还会做什么!你算什么七尺男儿?!就你这种人,还配做一朝宰辅,这大齐迟早会毁在你的手里!今日,我庄令涵因你而死,就算化作厉鬼,也……”
正在他又一次沉溺于她的温柔乡时,耳边忽然传来了几声尖利的指责,辨着音色,又似乎是他怀中尚未清醒的女人。
是她了,因为那声音里,口口声声称了“我庄令涵”——可她现在双目紧闭、眉头深锁,口中还断断续续地低哼,又哪里像是刚刚辱骂过他的样子?
况且,她还活生生、完整整地在他怀里,又怎么可能因他而死呢?
陈定霁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幻出了声音,这声音太过真实,让他以为她真的这样辱骂过他。这时,怀中的她却因为他的连番动作,悠悠转醒,他看着她迷蒙的双眼,忍不住问她:
“枝枝,你刚刚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声音?
她被他折腾到半夜,后来便体力不支晕了过去,这才刚刚转醒,却又发现他在不安分的动作,哪里顾得及听什么声音?
怕是他想用这淫词浪语挑弄她,才故意这么说的。
“君侯……我,我好累,浑身好痛,”她才不能上当,便只摇了摇头,想让他停下来,又咬了咬鲜红欲滴的唇瓣:“君侯,我求求你,能不能,放过我?”
陈定霁也被那刚刚的一声奇异的声响扰了兴致,想到以后,他不急于一时,便停了下来,又亲了亲她耳后红润的褶皱,道:“再多睡一会儿,我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
等到陈定霁终于起身穿衣,关门离去,庄令涵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她悄悄撩开他胡乱盖在自己身上的外衫,却只见那一片雪白之下,斑斓着好几处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
敏感之处,甚至能依稀看出大掌留下的红痕,想到他昨晚的无度索求和反复冲击,庄令涵脸红了好一阵,继而又陷入了深深的怅惘。
这一次,她已经真正地成为了他的女人,但和上一世一样,依然只是他的掌中之物罢了。
自己争了这许多时日,似乎什么都没有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