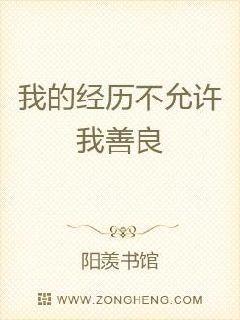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木屋(第1页)
木屋(第1页)
直到庄令涵被陈定霁放在了那张木板床上,她都还没有想得明白,他那句“病”,究竟指的是什么。
可陈定霁却抓着她颤抖的腕子,出乎她意料地,轻轻放在了自己的手腕之上。
这是,要她把脉?
他原本的面色尚算白皙,可长年累月的戎马生涯使他的肤色渐黑,只有被衣襟包裹住的不裸。露在外的地方,才是他原本的肤色。
这样的一张黑脸,本就不容易看出真实的状况,如今在这昏黄的光线下,“望闻问切”四个字,单是那个“望”,她就已经做不到了。
可是他的脉相,却是她一摸便明了了的。
与她上次一样,陈定霁也中了媚。药,不同的是,他入腹的剂量,比她当初那一口,要多上了不少。
一定是那宴席上,他的饭菜酒肉被不知不觉下了药,而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发作,他到底忍了多久?
可是她也无暇再思考这些,毕竟,她现在身边既无草药也无银针,不能像她上次自解那般,尚算轻松地渡过。
眼下,能帮他解毒的,只有她这个人,而已。
她咽了咽口中的津液,想了许久,才沉声道:“能当着君侯的面做怪、让君侯不知不觉吃下这害人之物的,恐怕世上,也没有几人了吧。”
她明明故作淡定,可他的目光一直纠缠着她。
这样直白的纠缠,炽热到使她有些害怕,于是,她便只能稍稍往后退了退。
想起他永远都用不完的精力和力气,若是他已服下这剂量不低的媚。药,后果如何,真的不堪设想。
她已经逃了很多次了,每一次都侥幸,没有让他得逞。
但显然,这一次,他不会再放过她。
她才堪堪挪动了两下,陈定霁便一把抓住了她的襦裙,轻而易举地将她拖到了他的面前。
她是待宰的羔羊,是砧板上的鱼肉。
喉头发堵,她连哀求,都突然说不出口了。
“那斛律太后想用下三滥的招数逼我就范,真是异想天开。”他的热息喷在她不知何时敞开的衣襟下、那早已颤栗的玉颈上,他的薄唇触到那紧绷的细线,又引来了她的一阵颤栗。
下三滥?她在慌乱中猛然想到,自己也曾用过那下三滥的招数对付他呀,可惜那时的结局,与预想的天差地别。
仅这一个走神,他已经解开了她对襟的盘扣,葱青色的抹胸与银红色的上衫交叠成趣,衬得她本就透亮的皮肤更加白嫩如雪。
陈定霁猩红着双眼,如珠如宝般多看了一会,然后倾身,用亲吻来代替了他逡巡的眼神。
“枝枝,你身上是香的。”他闷声感叹,不知何时已将自己的衣衫剥落,高大的身躯笼罩她眼前,她便更看不清楚了。
冬日的密林,本就应该更加湿冷几分。如今庄令涵在他的身下,却似乎感觉不到冷了,他的手他的吻,每过一处,都让她安稳如沐,温暖如春。
“君侯……”她被他锁在怀里,他用一只手便可将她轻易拿捏,她看着他略显急切的动作,呼吸忽然滞住,耳边全是他狂乱的喘息。
她知道,自己这一次无论如何都逃脱不掉了。
眼泪氤氲,徘徊在欲睁还闭的凤眸间,却始终没有如预料那般落下来。
陈定霁抬起了头,迷离地看着她,他漆黑的瞳孔里像是也蒙上了一层雾气,分不清是他的还是她的。
“唤我夫君,以后都只能唤我夫君。”他刻意加重了那个“我”字,是命令,是不容反驳的要求。
只这一句,庄令涵脑中的清醒便只能轰然倒塌,上一世第一次被献那晚的记忆,和眼下身边的每一个变化,全都纷纷扰扰、似假幻真地交叠在了一起。
一头被困了许久的猛兽,突然被放归山林,究竟会如何表现?
她如漂浮在海上的一叶扁舟,随浪翻打,遍寻整个宇宙,都找不到任何支点。
天地之大,又能去往何处安身立命?
她忘了自己何时唤出那声“夫君”的,从前世到今世,她真的只唤过他一人为“夫君”。
不过是个称谓而已,他在乎,她不在乎罢了。
反正翻山越岭的万里征途已然行到了此处,路的尽头到底是生的希望还是死的深渊,她根本无法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