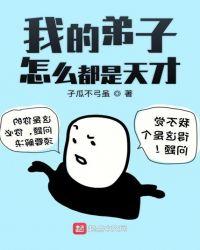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试药(第4页)
试药(第4页)
可是这与他们二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不想回答他,给他下一个侵略她的口实,只能不看他在这俯视下更为俊朗的眉眼。
她稍稍偏头,去瞧那窗牗上粗陋的雕花,想着该怎么开口,结束这场她不情不愿的闹剧。
但,她却发现那柏木的雕花上,竟然趴着一只巴掌大的蜘蛛,正自得地舒展着八只长腿,向她缓缓靠近。
庄令涵生平最怕这种玩意,连尖叫都来不及,想也不想,便慌忙地扑到了陈定霁的怀中。
陈定霁反倒被她惊了一惊,后退两步,才堪堪将自己和她扶稳了。
应该……应该没有爬到她的身上吧。
她惊魂未定,喘了好几声,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越界行为,连忙双手撑在他胸膛,想要分离这个拥抱。
但陈定霁怎么肯?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抱他,难道是因为他刚刚问她的话,真的让她放下了对他的抗拒吗?
他用力将她又抱得紧了些,将自己的呼吸贴近她的耳廓,轻声说道:“枝枝,你这几日过得辛苦,为了隐瞒身份,是不是差点连命都保不住了?所有人都不信任你,你喊破了喉咙,才能换来他们的一次回头,要是在我的身边,何至于此?”
他在说什么?他到底以为自己在说什么?
庄令涵在他怀中皱紧了眉头,可惜他看不见。
“原来枝枝你是想让我把你捧得高一点,像刚刚那样,对吗?”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若是你肯留在我的身边,我可以把你捧得高高的,让你成为整个大齐最尊贵的女人。就连那母凭子贵的斛律太后,在你面前也得俯首帖耳,听你的调遣。枝枝,这样,这样你满意了吗?”
她愣了,没想到他说出了这样的话,这是在给她承诺,还是在威逼利诱?
她一生所图,不过是家人平安,不过是凭着自己的双手,能让更多的人摆脱病痛——至于旁的,什么荣华富贵,什么功名利禄,她从来都不在乎,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过。
他以为她是什么,是要那所谓的“高”吗?在他那不切实际的构想里,她即使再“高”,背后也是他的一手扶持,是他的随心所欲,自己于他,也只是任他摆布的高贵木偶罢了。
他为什么就能笃信,她一定会欢天喜地地接受呢?
“君侯,你说到哪里去了?”她语气冰冷,浑身僵硬,“妾说过的话,从来都不会收回,妾说到做到。”
“你的哪句话?”他松了松,扶着她的肩膀,让她和他面对着面说话。
“我会亲手将你打入地狱,无论用何种方式。”她直视他的眼眸,刚刚哭过的凤眼,却闪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陈定霁看着眼前不为所动的女人,心中的怒火蓬勃燃烧,霎时便冲上了头顶,想要将她化成灰烬。
化成灰烬,她是不是就不会再让他生气了?
他是大齐最骁勇善战的军神,是最年轻的相国宰辅,从来只有别人求他,他从未求过谁。
初初与她相遇时,他看着她满眼都是夫君,尚能因为莫名的愧意,压住心中那与梦境交织的强烈的渴求;后来很快,她被他前夫休了,他知道自己不用在乎她可能在乎的名节,便放任自己,做了许多从前根本不会做的事情。
包括现在,用他能想到的、最能让她接受的方式,求她,求她心甘情愿地做自己的女人。
她不是想要一个位置吗,那他就把她捧高,像刚刚那样,她达到了她想要的高处,自然便不会再和他闹了。
做个乖乖顺顺的小女人不好吗?
就像刚刚,扑到他怀里那样。
那一刻,他是欢喜的,以为自己绞尽脑汁的想法,这么快便得到了她的认可。
可她为什么能那么快速就否决,为什么他已经放下了自己所能放下的全部,她还是不能按照他的想法来?
还说要杀了他,不止一次。
他的命若能那么轻易地拿走,那他就不是走到今日的陈定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