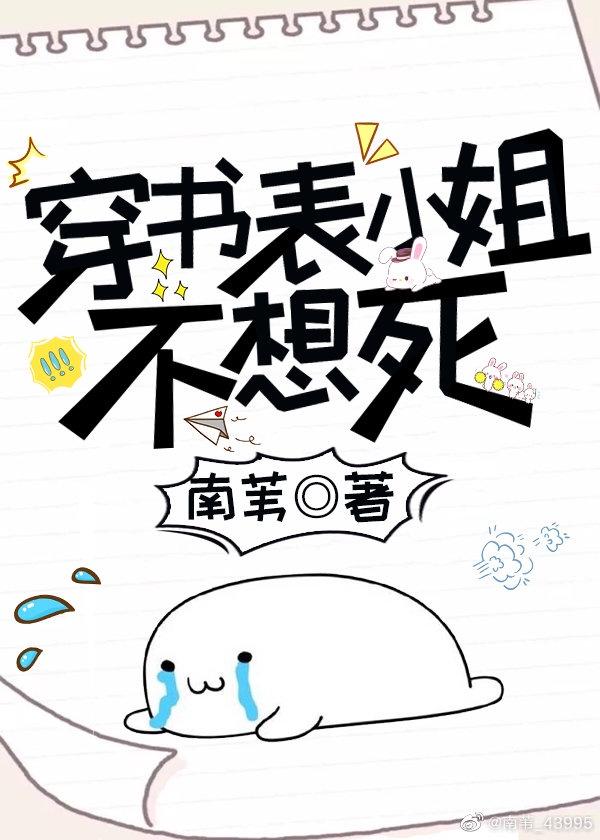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蕉鹿几事 > 第234章(第1页)
第234章(第1页)
杨叔的刀有血流下,向执安的眼看谁都蒙了一层红。
“大胆贼人!”身后有人发出怒吼,怎么算海先生也没这么快搬来救兵。
裴部一人策马,拉响鸣笛,横拦在向执安之前。
对面黑衣兵马并未怵他,下过雨的湿滑路面倒影出缠斗的众人,血污染黑了青苔哑砖,城中有狗吠鸡鸣,弯月被黑云藏起,只剩下众人湍急的喘声跟血腥杀气的蔓延。
黑衣人正要再起,裴部将钢刀对准了他们,向执安已然就剩下半口气,说“裴大当家,不该走这一遭。”
裴部闻言,也未往后看,只说“主子,裴某早不是裴大当家,裴某是载府点的睢州常备军指挥使。”
向执安叹了口气说“裴将军,不值当。”
裴部的刀已然开始厮杀,老马已经不复当年的英勇,看起来甚是力不从心。
裴部使出浑身解数拖延时间,终于在老马浴血之时等来了周广凌。
黑衣人在马踏声来之前四处藏匿,屋檐上不知何时有人伏击,三支箭弩在阴暗中射出,目的很明显,是向执安。
轻巧的装弩声都逃不过杨立信的耳,挥手刀身发出如风铃般清澈的声响,两支箭弩应地。
杨立信护着向执安说“杨立信不能再没有主子了。”
没人发现,一只小箭擦过杨立信的脖颈,留下一道轻微的血色。
向执安由杨立信背着,终于见到了策马而来的海景琛。
“海先生深藏不露,何时学的骑马?”向执安都快死了,还佯装无事发生。
众人进了小院,裴部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在人海中。
向执安进了院子就开始发起了高烧,这高烧来的着实迟了一些,杨立信一边不断的用温水擦拭,一边儿煎着药汤。
海景琛坐在这屋里的团凳上,就这么看着向执安,其实海景琛没见过这样的向执安,从他被捞走放置向执安身边,能见到的就是一直如胜券在握般的风雪催打不弯脊背的那个少年。
是传闻如女子媚却比侯爵贵的公子,是手执蕉鹿软刃可厮杀疆场的英豪,也是想学名伶唱曲儿水佩风裳的小君,亦是能镇守八方群雄逐鹿天阙的谋臣。
是书生,亦是将军魂,是文臣,又怀英雄骨,是刀剑难屈的九州枭主,亦是窥生机破死局的人间棋手。
但是他如此破碎,摇摇病体,以血肉扶将倾的厦,此刻才算真的将他掩埋在废墟之下。
海先生的背弯了。他不知道此刻该做什么,郃都的棋盘,他第一次举棋不定。
杨立信忙活完这些,坐在海景琛的身边。“海先生,在想什么?”
“在想是带着主子逃到云山1去,还是带着主子逃到棉州去。”海景琛看着杨立信的眼神说“如今日刺杀之事,日日都会来,郃都现下没有了皇嗣,天下之人尽可逐鹿。”
“海先生,你不是这样想的。”杨立信拧干了帕子,为海景琛擦拭着手上的脏污,说“若是没有司崽,你便不与主子一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