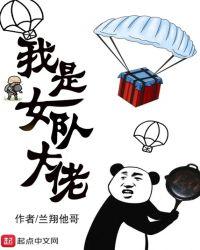墨澜小说>里正的自我修养 > 第 77 章(第2页)
第 77 章(第2页)
如今村中每日安排轮流巡夜,葛歌今夜是排到上半夜,后半夜左右无事,她也就不怕喝醉耽误事儿了,皱着眉头把碗里剩下的那小碗喝完,将碗往前一递:“崔先生也不遑多让!再来!”
“再来!”崔永濂单手提起酒坛,哗啦啦给俩空出来的酒碗都满上了。
两个都是心里藏了许多事儿的,又是一拍即合的性子,这你一碗我一碗的,喝了三碗,两人皆有了三分醉意,便暂时歇会儿,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儿。
“崔先生,你、你说这世道得乱到何时啊?”葛歌秀气地打了个小小的酒嗝儿,嫌坐着没地方靠背,索性反过身子盘腿席地而坐,靠在圆凳边儿上,抬头望着满天繁星,小声喃喃道:“我不想死,我想回家…”
葛歌力气再大,打人再痛,可杀人还真是头一回,想到自己双手沾了鲜血,葛歌也不看星星了,望向也学着自己瘫坐在地的崔永濂:“崔先生你呢,杀过人吗?”
“杀过。”崔永濂低头又啜了一口酒,眯着眼回想数年前,自己第一次跟父亲上战场的场景。本以为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早已看开,却原来第一次见到血肉横飞的震撼与厌恶早已刻在骨髓。
“你不怕吗?”
“怕,可我若不杀他,便是他杀了我。”崔永濂仰头喟叹一身,苦笑道:“葛歌,世道如此。”
“世道如此,我们就也要如此吗?”葛歌突然坐直了身子,直勾勾地看向崔永濂:“生灵涂炭的世道,这是你想要的世道吗?我却不想要,我想要政治清明,人命值钱,百姓安居乐业,人人能仓廪足而知礼节的世道。”
“安居乐业,仓廪足而知礼节,谈何容易?”
“如何不成?所谓不破不立,如今这世道是烂到了根子,你再怎么施肥浇水都没救的了,还不如另种一棵新的!”葛歌仰头一口饮尽碗里的酒,大叹一声:“好酒!”
这是崔永濂第一回与葛歌谈论到民生天下,政治世道。听小姑娘这般豪横的发言,崔永濂都忍不住侧目看向她,唇畔的笑却多了一丝轻松了悟:“不是方才还哭着说自己杀人了,这会子是酒喝多就狂得天下都成你的了不成?”
“你说得对,我若不杀他,他便杀我们,这般想就不怕了。”葛歌两颊印上了浅浅的红晕,双眸半阖未阖地,应道:“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不信甚天选之子,我只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当官儿当皇帝都一样,不为民做主的就该回家卖红薯去!”
崔永濂听完这话,目光深邃地望着已歪着头睡着的小姑娘,他才晓得这小姑娘,真是个敢想敢说的小姑娘。
见她要倒,崔永濂连忙将酒碗随手放在地上,另一手稳稳扶住葛歌的脑袋。
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这小姑娘说这一番话把我的心闹得乱哄哄的,结果自己还倒头就睡着了!崔永濂笑着看了眼葛歌,空出来那只手又将放在地上的酒碗端起来,慢悠悠地独酌。
葛家如今在吴用老两口的管理下,上下井井有条。不过鸡啼时分,四处房门轻声开启,炊烟袅袅迎来了新的忙碌的一日。
明芝望着院子里的狼狈,有些不知所措地拉了拉同样没回过神来的姐姐:“姐,咋办?”
“…你在这儿守着,我去请刘婆婆过来。”明佳看着随意倒在石桌那儿的酒坛子,空气中还夹杂着淡淡的酒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交代了妹妹一声,自己赶紧往前院去寻吴刘氏。
吴刘氏听完明佳小声俯到耳边说的话,眼神也有些不可置信,交代了句灶上干活儿的人仔细些,自己匆匆随着明佳到了后院。
站在距离还沉睡着的两人不足十步之处的吴刘氏看着俩脑袋挨着脑袋,就坐在地上睡着的俩主子,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什么好。又瞧着天快亮了,也顾不得旁的,上前轻轻拍了拍葛歌的手,小声喊道:“主子,咱回房睡罢?”
“唔?哦…”沉睡着的葛歌意识全然没有清醒,就被用力搀扶起她的吴刘氏与明佳合力扛回了房里炕上。
躺平在炕上的葛歌抱着枕头还无意识发出一声舒坦的喟叹,连眼睛都没睁开过。
搞定了一个,还有另一个。
站在院子里的吴刘氏只恨不得一脚踢醒少将军,这孩子咋都十七了还不晓得顾忌些呢?若叫外头人晓得了,那小里正的名声可不都没了?
不过还是顾念着崔永濂,叫明佳姐俩寻了间干净的房间,吴刘氏自己又往前院回,悄悄叫来吴华吴文哥俩把醉醺醺的崔永濂给扛到那房间去,自己再叮嘱一番这四个孩子,谁也不准往外漏一句。
几个孩子听了,连连点头。忙完一通的吴刘氏才算松了口气。
作者有话要说:请注意,此时的哥儿才十四,不许多想!直女还是笔直笔直的!
我们这能叫有奸情吗?不能!我们这叫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