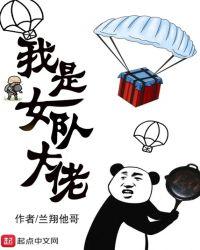墨澜小说>里正的自我修养 > 第 77 章(第1页)
第 77 章(第1页)
红脸汉子捂着自己不断渗血的胳膊,心里是真的发虚了:这还隔着少说二三十丈,那小子竟能一箭伤了自己,再看对面跟在那小子后边儿的村民,一个个气势十足。
反观自己这边儿,经历过方才一回的人心本就散了大半,好容易叫自己给拢起来,这会子又被对面那小子先射伤自己,再说出那般的话,人心算是彻底散了。
紧跟在少将军身后的吴文手里紧紧握着自己来云州前爹给自己准备的佩剑,一心要护住少将军。紧张了两刻钟,对面那二三百人竟不战而逃,见对面那些人全都走了,吴文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不战而胜的华新村村民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哦!哦!”
崔永濂心里也是浅浅地吁了一口气,幸好,幸好。
虽是松了口气,不过也没敢真的放松,崔永濂交代巡逻的人继续巡逻,其余村民则各自归家。
听到外头轰然动静的葛歌心急如焚,却被吴刘氏盯得紧紧的,连第二进院子都出不去。好容易等到崔永濂回来了,连忙迎上前去:“如何?”
“都散了,巡逻队还在巡逻,若有情况我们也会及时晓得。”崔永濂将葛歌用得只剩七支箭矢的箭筒及弓还给她,浅叹一声,道:“这批应当不会再来了,只是若再这般乱下去,我也不晓得能抵挡住几回。”
说起如今乱象频生、民不聊生的世道,崔永濂嗓音有些哑然,为将为士者,不能抵御外敌,还要在国土内与同胞自相残杀,这叫什么世道啊?!
葛歌看出他面上的纠结与痛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出来,只无奈地叹了一声。
外头世道一日乱过一日,多地流民□□问题尚未解决,南楚州郡又爆发绿林起义,为首的都是打家劫舍的悍匪,不过短短半月竟连占两座城池,所经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怨四起,怨声载道。
偏居一隅的崔永濂,人虽没离开过华新村一步,可外头的消息却如同插了翅膀的鸟儿一般飞入自己耳中。
“如今外头乱得很,国都却是一片歌舞升平,老奴接到国都密信,国君不日前才耗费巨资要建造长生台,以求长生不老。”夜深人静时,吴用将自己收到的消息禀告给少将军知晓:“如今国君对武将防备之心太大了,派兵平复南楚之乱,竟叫一个连国都都没出过的宦官随行监督!”
收到父亲来信,终于查明自己受伤缘由的崔永濂对这不顾苍生的国君早已没了丝毫敬意,只冷笑一声道:“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吾等只看着舟何时倾覆便是了!”
“少将军!”吴用低声惊呼出声,少将军方才看完西南送来的密信后就有些不妥,如今竟还讲出这样的话,莫不是…大将军在信中提了什么?
崔永濂无声地叹了口气,苦笑着摇摇头:“无事,这会子也不早了,您老也早些回去歇着吧。”
主子不说,吴用也不再多问,担忧地看了眼少将军后,吴用才无声地退出东厢房,提着灯笼在葛家四处巡过一回后,才往西厢房回。在西厢房门口又遇着出去巡夜披了一身雾水的葛歌。
吴用笑呵呵地与向葛歌请安,问到:“时辰不早了,我送主子回去安歇吧?”
“无事,我自己回去便成。”葛歌随意地摆摆手,吴伯也是上了年岁的人,在自己家里也不会有啥事儿,便叫吴用早些回去歇息,自己提着灯笼往东厢房旁的甬道走,而后拐入第二进院子,往自己房间回。
却被坐在院子东角葡萄架子底下一个黑影吓得葛歌一个激灵,举着灯笼照明:“何人在此处?”
“葛里正,是我。”原来是与吴用说完话后,躺在炕上烦躁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出来在葡萄架子下坐着思考人生的崔永濂。
见是崔永濂,葛歌长长吁了口气,嗓音清沉,状态轻松了不少:“如今已近三更时分,崔先生还不安歇吗?”
自打七月里抵御流民一事,原还有些生疏的两人如今变得亲近许多,本就也是差不多年岁的人,坐到一处倒也能说到一起去。
透过昏暗的灯笼光亮,葛歌瞧他一脸凝滞,郁郁寡欢的,想了想,便道:“我那儿还收有上回生辰宴喝剩的半坛子酒,不知崔先生是否赏光共酌一杯?”
“既有美酒,一杯如何足够?当瓢一大白才是!”崔永濂露出今夜第一个由衷的浅笑。
前边儿院子住的人多,葛歌悄摸摸溜进厨房取了酒与碗,与崔永濂一人抱酒一人捧碗,索性往第二进的小院子去,那里边儿也有石桌石凳,只有远远住了明佳明芝小姐妹俩,小姑娘睡得沉,也不怕吵着她们。
八月初秋,如墨夜空中点缀了漫天繁星,寂静世间,只有蛐蛐儿不断叫唤着,伴随着两人碰碗的声音,格外清脆。
“哈!好辣!”每回喝陈家的酒,葛歌都会被辣到,可偏生久了不喝,还真有些馋。
在军中长大的崔永濂酒量自然也不会差,咕噜咕噜几口便喝完了葛歌方才给他倒的那半碗酒,见葛歌被辣到整个人都皱成个包子模样,咧嘴笑了笑:“葛里正好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