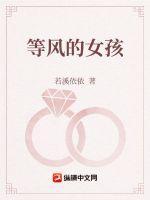墨澜小说>李李翔浪漫言情全集(共15册) > 第十七章情窦初开(第2页)
第十七章情窦初开(第2页)
下了晚自习,一伙人围在一起还是不肯走,叽叽咕咕商量着要不要出去玩。有人犹豫说:“后天就高考了,不大好吧。”韩张头一个说:“怕什么,许魔头都让我们别再看书了,总要找点儿事做。钟越,你跟我们一块去,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娱乐学习两不误,游刃有余。”又转头问何如初,“你去不去?”
何如初便问他们大半夜的打算去哪儿。五六个人商量了一会儿,说去桌球厅。毕竟还要高考,不敢玩得太过分,只好选了项轻松的消遣。因为学校附近就有一家桌球厅,离得近,她便点头,一块儿去凑热闹,说好输了的人要请吃东西。
何如初对桌球还挺熟悉。在她小时候,爸爸工作不忙时也喜欢玩一两局,常常带她在身边,赢了就给她买好吃的。所以一进桌球厅,她就有亲切感。男生选了球,她站在旁边看,兼当裁判员。
钟越样样优秀,没想到对桌球却不大擅长,开球都没开好。
其他几个人顿时来了精神,能把钟越打败,是多大的一项殊荣啊——尽管只是桌球。所以人人都要求跟钟越来一局,自信心空前膨胀。倒是韩张,是个中高手,打得一群人落花流水,哀叫连连。
何如初在一旁看得直摇头,拍手笑说:“钟越,你直接请韩张吃东西得了!”钟越无奈地叹息,扔下球杆苦笑着说:“你们想怎么宰我一顿?”三更半夜,小店都关门了。大家都饿了,只好去二十四小时通宵营业的超市一人拿了一大包绿豆饼,边走边吃,到路口各自散了。
钟越送何如初回家。两人沿着街道慢慢走着。何如初沉吟许久,还是问了出来:“晚上老许找你,说什么了?”钟越回头,看着她微微笑,反问:“你先说他找你说什么了?”何如初脸忽然红了,幸好是夜里看不到,她清了清嗓子,说:“没说什么,只说我很不错,要有信心。就这些。”说完转头问他,“一年来,老许从来没找过我。你说他这话什么意思?”
钟越回答:“鼓励我们的意思。”说完,停下脚步,看着她不说话,眼中似乎别有深意。何如初还来不及问“鼓励我们什么”,抬头看时,已经到小区门口。似乎该分手了,两人却都没有立即离开的意思,总觉得有些话搁在心里没说,待要说出来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钟越提议:“我们再走一走。”她傻傻地点头,跟在他身后
,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不言不语。灯光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慢慢地两个人影渐渐重叠在一起。钟越停下脚步,等她并肩而立。
安静的夜里,语言似乎成了多余的累赘。许久,钟越问:“打算报考哪里?”那时还是考完试后先估分再填志愿。她反问:“你呢?清华大学?”他点头,他向来是最好的。
何如初摇头:“我不行。”清华大学对她来说,太有难度。上临一中一年能有几个人考上清华大学已经了不得,有时候一个都没有,尽管每年都有学生考出来的分数高得吓人。高考,除了成绩,胆识和运气同需兼备。竞争太过激烈。
钟越说:“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就很好。”他说的都是北京的大学,其意昭然若揭。她闷闷地说:“我爸爸似乎有意让我去上海。他曾经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钟越沉默了会儿,说:“还是来北京吧,毕竟是首都。”声音虽轻,意思却很坚决。
她低着头不说话。
钟越忽然牵住她的手,说:“我送你回去。”语气看似镇定,其实手心全是汗。何如初的心早已乱了,也没有挣扎,任由他拉着走,怎能发觉他隐藏的激动?
两人就这样手拉着手安安静静走了一路。短短几分钟,却似一生那么长久。
重新回到小区门口,两人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钟越说:“何如初,你是在二中考?”她点点头,按学号她分在上临二中参加高考。他喃喃道:“我在一中。”意思是说,高考这两天都碰不到了。
何如初没有说话,女性的直觉是那么的敏感。果然,钟越结结巴巴地说:“何如初,我有一个要求…”见她根本不敢抬头,钟越鼓励自己说下去,“我能不能摸摸你的头发?”
虽然十分意外,但是何如初却大大松了一口气。如果钟越要吻她,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只是摸摸头发。虽然她觉得这个要求很奇怪,还是点了头。
钟越颤抖着手抽出她的发带,如云的秀发似瀑布蓦地泼下来,灼伤了他的眼睛。他尽量使右手平稳轻柔地穿过她的长发,感觉她的头发很是柔滑细腻…他把她的长发由上到下轻轻梳了一遍,手中的触感、心中的情感无法用言语形容…
以后,这种感觉只有在记忆里才找得到。有些东西,当时不知道,等很久很久以后才蓦然明了,曾经在一起的日子是最美丽的。只是再想重温,却不复重来。
他的手在她发间停留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匆匆理了理,就拿开了,如穿花蝴蝶,蜻蜓点水,一闪而过。何如初不解他怪异的举动,问:“我头发乱了是吗?”
钟越手足无措,半天才说:“晚安。”匆匆走了,连发带都
忘了还给她。
何如初倒没有多少旖旎浪漫之感,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懊恼,今天为什么没有洗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