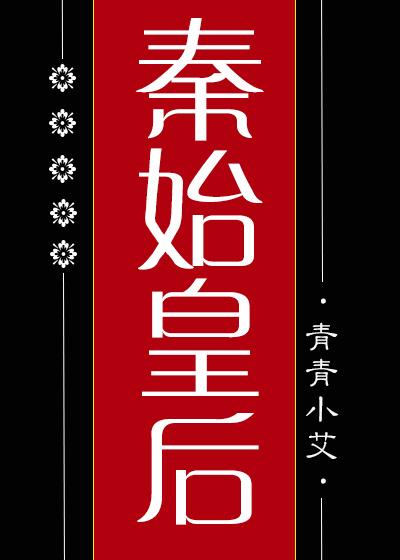墨澜小说>芳华怨:烟花易冷为谁折腰(更新中) > 一斛珠(第28页)
一斛珠(第28页)
我冷笑:「容督主好大的胆子!」
他却像是听不懂我话里的愠怒,只是沉声问我道:「你方才与柳如年见面了?」
虽是问我,但语气分明笃定。
我蓦地用力挥开他的手,防备的看他一眼:「与你何干。」
「那日我给你密信,你我都知道今天本该出征的人不是赵敬之。」
他凝着我,目光诡谲沉闷幽幽:「六六,你护着他?」
「护着他又怎样?」我心头慌乱,面上却毫不示弱。
我讥讽道:「不护着他,难道我护着你不成?」
容时的脸色白了几分,看上去有些脆弱。
他问:「你喜欢他?」
声音苍白到快要破碎。
我不说话。
像是无声中的一种默认。
容时凄笑,低声自言自语道:「也是,当初你就写信让他救你,也是……」
我被容时那双嫉恨深邃的眼睛盯得背后生寒,几欲想走,却不想他如此大胆,忽然几步将我逼至宫墙退无可退。
容时俯身,将我困在他的阴影里,修长白皙的手指轻轻捻过我额角滑落下来的一滴冷汗。
我背后寒毛倒立,惊呼道:「容时你别在这里发疯!」
容时轻轻掀起欣长的羽睫,眼底一片猩红,瞳孔墨黑毫不掩饰其中化不开的阴暗偏执。
他笑,仿佛坏掉了一样,美的触目惊心却又似厉鬼索命。
容时凑近我,低语道:「六六,我早就疯了。」
20
尽管那天之后容时并没有再为难我,可是临近月末,东厂那边一反常态,始终安安静静,没有派任何人给我送来压制血蛊的药引。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疼痛不出意料渐渐加重。
饥饿的子蛊得不到补给,深埋于我的血肉里开始变本加厉噬咬我。
一如两年前那次。
我知道这是容时在逼我向他低头。
钻心入骨的痛一旦得不到缓解,只会更加残忍的日夜撕扯我每一寸血骨,要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可我始终不肯求他。
赵恒钰早就察觉到我的异样,为了避免他心生端倪,我不得不对外放出消息,称病拒绝会面任何人。
距离月初只剩下一天,可我最终还是没有挨过去。
刀割骨头的绝望撕裂我的倔强,我崩溃地赶走了所有人,尖叫大哭着砸烂了寝宫里所有的东西,如同倒在废墟里奄奄一息到的野狗,只能做到蜷缩成一团流泪颤抖。
视线忽明忽暗,意识也变得神志不清,恍惚间,我竟然一时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
直到模糊的视线触及到寝宫红漆门外一道微弱的白光,我看见那人缓缓向我走来。
他抱起苟延残喘的我放到床榻上。
子母蛊似互相存在感应,痛感从他近身起就稍作停歇,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体内顿时暴虐般涌上来的嗜血感。
我猩红着紧紧盯住容时,眼底全是渴求流淌于他身体里的血液如同上瘾。
用尽最后一点残存的理智,我粗粝的声音压过喉咙生生逼出一个胁迫的「滚」字,像是被火烤过,沙哑而难听。
容时默不作声,像是没听懂一样。
他抬起手,衣袖堆积下滑,露出一截修长却满是刀伤疤痕的小臂。
那些伤以前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