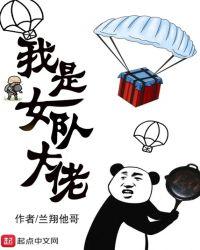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嫐(沟头堡的风花雪月) > 第35章 梦一场(第6页)
第35章 梦一场(第6页)
而从文娱路走到家属院,再由家属院走出来,没有争吵也没有过都逗留,不过她却一直在问着自己一个问题——内个人真的是自己托付一生的人吗?
既然是,那为啥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她琢磨不透,也越来越看不明白,而且发觉二人之间的话题变得也越来越少,这究竟是自己太过霸道了呢还是对方太虚了呢?
她知道没病死不了人,然而困扰在这无解的局中,谁又会给她答案呢。
“好意我心领了。”沉思半晌,灵秀回绝道。
咂摸着灵秀话里的意思,他知道人家用不上自己,也知道自己太过自作多情了。
“那个女的跟我二叔有些不清不楚吧。”察觉到似乎说错话了,忙又改口道:“瞅我这鸡巴嘴,净瞎秃噜。”边说边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灵秀看着坡下的青草怔怔发愣,缓了好半晌,站起身来:“你回去吧,我也该走了。”
看着灵秀跨上自行车车,顾长风腾地站了起来,朝她喊了声“婶儿”。
长堤上,树像水中的浮萍,一直在抖,灵秀朝北而去,没再回头,像上礼拜那样独自一人朝着陆家营的方向骑了过去。
对于这阵子闺女的频繁往复,柴老爷子曾问过原因。
“吵架了还是咋的?眼跟兔子似的?”
灵秀不答。
柴老爷子又问,问着问着就急了。
“有家有口的,什么事儿不能解决?”这么多年他从未见过姑娘这幅模样,“你倒说句话啊?!”灵秀仍旧不答。
老伴儿见状,忙打圆场。
“小妹你怎了,倒跟你爸讲讲啊。”
这边劝完,内边又劝老头子。
“容她喘口气,这么急干啥!”
后来沈怡过来,老爷子才得知具体情况。
“当初你不也这样儿吗。”
解释开了就又问灵秀外孙的脚碍不碍事,直嚷嚷着要去沟头堡看看呢。
周三内天晌午灵秀把情况又彻底给二老解释一遍,就如现在,她说:“直说在他娘娘内边住着呢,骗你们干啥,又不是什么大事,都甭过去。”
又告知二老说儿子班里的同学来了,明儿指不定要去哪呢,撒了个谎。
本来这压在心头的事儿想跟沈怡诉诉,听闻说好几天都没在家,连大鹏都跑他爷那了,就是不知这姐妹儿跑去哪了。
灯熄灭之后,灵秀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其时圆月当头,身周都响起了呼噜声。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梳的油头,而且又穿上了内件青花瓷色的高领旗袍,更为古怪的是,居然还是在船里面。
她扫视着四周,确实是置身在船里,晃悠悠的。
面前摆着那把瑶琴,一切如旧,她便颇为熟练地把双手搭在上面,在氤氲的香雾中,挥动起双指来,琴声中她想看清对方的脸,却怎么也看不清楚,她心说算了,至于说为何要算了呢,却始终分说不清,于是便在琴声之下跟着一道和了起来。
山青青水碧碧
高山流水情依依
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啼
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声音,怎把电影里的东西搬出来了?
不等细琢磨,外面的天色便似乎暗了下来。
船儿一直在微微晃荡,她起身把被褥铺在了脚下,她听到了“革命尚未成功”,直到宽衣也始终没看清那人的脸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吹熄了灯,耳畔缓缓而起的是一股股淙淙流淌的水声,时而婉转缠绵,时而又悠远绵长,令人分辨不清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