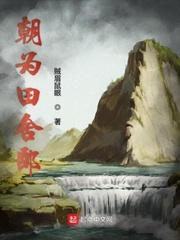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景云阕 > 第119章(第2页)
第119章(第2页)
她得意地努努嘴,“郎君不如来豫王府抢人。”
“三郎。”没有思索,没有挣扎,满目黑瞳里,这两个字自然而然地溢出嘴角。
“谢韦姨!”眼前的李隆基一脸雀跃,显出几分与年纪不符的天真轻快。
“听闻韦姨从前就住在这里,我阿娘的屋室是那个”,他抬手轻指,望着不远处从敏的居室说道,“如今相王府女眷不多,豆卢孺人和王孺人皆已安顿妥当,这个院子韦姨一个人住着也宽敞。”
“这些……都是你布置的?”我实在吃惊,他一个出府居住的郡王,怎么会管起相王府里的琐事。
“阿耶受陛下托付,要时常去国公府照管修缮扩建事宜,自家王府的事就只能叫我们兄弟看顾了。”
“国公府?哪个国公府?”
李隆基唇边含笑道:“从前的周国公府,陛下特意赐给了义兴王,说是不能没有成婚的府邸。”
李重润死后,陛下便为义兴王李重俊与弘农杨氏赐婚,照理也确实应该婚后开府,离居东宫。
可他住的竟是从前武承嗣的府邸。
“三郎可知国公府修葺多久了?”
“阿耶回到长安不过几日,国公府自然是刚动工”,李隆基挑眉道,暗含得意之色,“我府中还有些杂事,韦姨若没有别的嘱咐,我便先回去了。”
我草草点头,心中只余难捱,待他走远后,攥紧了衣袖中的东西,转头吩咐阿鸾备马。
从长乐坊到永宁坊,一路疾驰,我在马背上,望着摇摇晃晃的长安城,觉得如堕烟雾,茫然自失。
我不知道为何一定要来周国公府,也不知道为何这般急不可耐,就像我不知道为何隔着整座洛阳城,我非要去持明院。
我从未来过武承嗣旧时在长安的府邸,但他为周国公时已目中无人,所以当我亲眼所见国公府的布局大小与亲王府无异时,倒也没有意外。
拿着陛下近侍的龟符,自然无人阻拦,我一路直入内院,停在了正房居室的门外。
做工的仆役正将房中的书案坐具一一搬出,我无暇顾及这些,只是一步一步迈进房中,迈进纠缠了武延基大半生的梦魇。
就是在这里,他蒙着武延秀的双目,自己躲在暗处,眼睁睁地看见父亲亲手勒死了母亲,为的不过是尽早当上太平公主的驸马,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
三年,他为母亲报仇不过三年,他从噩梦中转醒不过三年。
袖中藏着的东西被我缓缓抽出,无数的记忆铺天盖地地卷来。
他在我的怀里奄奄一息,将自己的半卷弓弦递给我,说他不后悔。
他握住我的手,将半截弓弦塞进其中,让我用它来记住他。
两段弓弦,一半一半,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我捏着一端,将它们重新系在一起。
“武延基”,我轻念着他的名字,不需要这个,我也记得你。
“团儿。”
熟悉的柔润音色从身后传来,我猛地回头,果然看到李旦长身玉立,隔着数步之远,不动声色地盯着我。
“你怎么在这儿?”我脱口而出,却忽然想起他本来就该在此,不禁哑然失笑。
“这句话,该我问你吧?”他轻轻抬腿,一步一步地迈向我,眼中冷意渐浓,“你和武延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你就这么放不下他?非要到他从前的家里来看看?”
我被他这样少见的诘问所惊,倒觉得好笑,反问他道:“我两次嫁给你,加起来也不过四年,你真的要问我和别人都发生过什么吗?”
“团儿……”
“况且”,我打断他,“你有妻妾近十人,我何时问过谁在你的心里最重?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来指责我和武延基的关系,这对我公平吗?”
“团儿”,他的眼中终于波澜四起,眉心的剑纹愈加深刻,“你该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武延基死了,他已经死了,没有葬礼没有祭文,我都不能专程来这里悼念他吗?”
“可你悼念的是他!不是他们三个,团儿,你知道这其中的差别,你知道这对我……”
哐啷一声,府中的仆役不慎掉落了手中的金银平脱镜。
“出去!”他极不耐烦地吼道,吓得仆役一个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