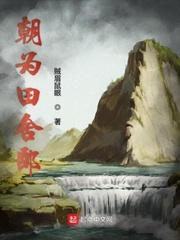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景云阕 > 第119章(第1页)
第119章(第1页)
“上元元年,当时的陛下加尊号为天后,与先皇并称二圣。团儿”,婉儿了然一笑,“从那时起,陛下就说过,她已经不算一个女人了。”
“是啊,她要在满是男人的朝堂中摸爬滚打,就要把自己先变成一个男人。”
“团儿,邵王和魏王的死,你就这么过不去吗?”
我仰头看天,苦笑一声道:“太子终究会是一个帝王,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只可惜我阿姊,她还真的只是个女人。”
“莫说太子妃,就是一直陪在陛下身边的公主和你我,还不都是女人么?”
婉儿的这句话,让我想起在寿光县主府,我因乔知之一事百般彷徨无措时,李旦曾劝慰我,公主和婉儿与陛下不同,我亦如此。
话是不错,可我实在不敢确保,李显登基之后我们三人的处境如何。
“陛下既然有意,只怕日后我们会更常在东宫相见了。”婉儿见我半晌无话,又微笑着对我说道。
我知道她的暗示和对我的担忧,不愿再让她烦扰,只抱以一笑。
十八年前长乐坊的豫王府,只是稍加修葺,便是如今的相王府了。
齐郎遣人来问,我是否还愿住从前的屋子,我没有多想,只随意地点了点头。
房中陈设变更,书案坐具一概换新,已找不出旧时的模样。
“禀孺人,侍婢在清扫时拾得书信一封,不敢随意处置,还请孺人过目。”新分来房里的侍女阿鸾说道,恭敬地托举着一个缄札。
纸边发黄,已是有些年头的样子。
我疑惑地接过,从中取出两张已有些薄脆的花帘纸,小心地展开,好奇地向其中文句看去。
“豫王,展信佳。
离别数月,王府诸事平顺,近日趣事良多,提笔道来,忍俊不禁矣。
芳媚习马术,屡屡戏弄平简,安郎君虽年长,似难招架。
吾与从敏私换男装,至西市食胡饼毕罗。吾不喜甜,从敏极爱樱桃毕罗。偶遇太子及吾姊,往胡玉楼观歌舞。
素闻平康坊金迷纸醉,歌伎舞姬,有倾国倾城之色、摄人心魂之姿。他日郎君归家,可愿携我二人同去?
惟愿天皇陛下平复如故,享南山之寿,此亦天下万民之盼。
妾韦氏永淳二年十月书,顺颂时绥。”
屋内无人言语,我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一声又一声,明明近在耳边,却觉得遥远无边。
“孺人这是怎么了?婢子有罪。”
我如梦初醒,双手轻触脸颊,才发觉早已泣如雨下,转头看着跪在石砖上一脸慌张的阿鸾,强笑着说:“起来吧,与你无关。”
“孺人可在?三郎特来请罪。”门外传来低沉有力的郎君音色,阿鸾匆匆起身开门。
李隆基一身素服,垂手立于我的房外。
他微微抬头,眼角眉梢已敛不去重重的图谋和算计,但漆黑的眸子仍泛着光。
神异而形似。
“韦姨,你可会原谅我?”
我一阵恍惚,永淳二年的从敏还未走远,我就真的看见了她的眼睛。
“临淄王,你这是做什么?”
李隆基半跪而蹲,对着我郑重施礼道:“从前三郎年幼,对韦姨多有误会,还望韦姨看在阿娘的面子上,不要怪罪。”
“临淄王,我……”
“韦姨可愿向从前一样唤我三郎?”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李隆基突然就不再记恨我,理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其中蹊跷,可……
身穿窄袖胡服的从敏歪着头,对着我巧笑倩兮,“郎君实在轻薄,闺名怎敢相告?”
“莫不是已为人妇?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