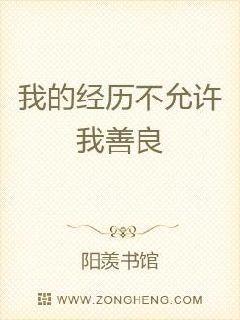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新安笔上 > 第八十二章 暮年丧子(第1页)
第八十二章 暮年丧子(第1页)
南风斋被一群家丁围得水泄不通,家丁个个身材结实,面色不善。
南风斋内徐竹已年过古稀,趴在徐台的尸身上泣不成声。
周澍同崔仪立在一旁,念在他年老丧子,相顾无言。
徐竹在管家的搀扶下,缓缓站起,眼中难掩悲伤,看向周澍,质问道:“周少卿既在寺中,吾儿又怎会死?”
周澍道:“如徐尚书所见,令郎脖子被撕扯,断气而亡,按照伤口来看,非是人力,乃是青鬼杀人,望徐尚书节哀。”
徐竹将拐杖狠狠一杵,愤怒之中带着嘲讽,道:“青鬼?周少卿断案竟靠鬼神之说,可笑京城上下称你为周郎,如今竟用鬼神诓骗老夫!”
周澍反问道:“徐尚书不信鬼神之事?寺中上下皆知青鬼,有人亲眼所见青鬼杀人,徐尚书如何不信?”
徐竹冷哼,满是皱纹的脸阴沉下去,“鬼神之说皆是虚言,如今吾儿死得不明不白,周少卿不去查杀吾儿的凶手,竟妄想将鬼神之说强加于老夫,周少卿如此是否有违刑狱官查案断狱之责?”
崔仪见他嘴脸不改,方才敬他是看在周澍面上,如今他儿子尸身在旁还如此咄咄逼人,崔仪忍不住便道:“徐尚书既说鬼神之说是虚言,那夜行游女之时为何偏偏信了,还要奏请圣上以五十童男童女祭祀?这是巴掌不打在自己脸上不知疼,如今寺内确有青鬼害人,尚书为何不信?”
徐竹指着崔仪,被
呛得声音颤抖,“这,这怎能相提并论?”
管家道:“周少卿,崔世子,夜行游女之事已是满城风雨,我家家主是为圣上分忧,平息百姓恐慌才请求祭祀,实为无奈之举,祭祀之事已由太史局占卜观星象,并不不妥,此事也经由礼部斟酌考量之后方才初定,虽未祭祀,京中流言已平,如此夜行游女一事也怪不得我家家主。”
崔仪听得发笑,“如此说来夜行游女之事能平,皆是因徐尚书奏请祭祀,而非刑部侍郎抓获装神弄鬼的贼人?”
管家从容道:“自然不是,鬼神之说实为无奈,周侍郎既抓获背后之人,夜行游女也并非鬼魅,如此这寺中又怎会有青鬼?一切皆是人为罢了,望周少卿替我家二郎讨回公道。”
管家郑重叩拜,崔仪算是看明白徐竹带管家来是何用意,徐竹丧子,说话难免有失偏颇,管家心思深沉,说话行事都是跟着徐竹这些年练出来的,徐家能有他这么个管家,能抵上十个徐台。
周澍将人扶起,道:“此案自是要查,寺中被青鬼所伤之人甚多,一时毫无头绪,后日圣上便会到寺中祈福,子熠自当尽力而为。”
徐竹听出他言下之意,要查也得在圣上祈福之后查,要查也要分个先来后到,被青鬼所伤的人多,不知何时才能排到徐台。
“周少卿未免太儿戏,查案只论证据,何来先后之说?后日圣上祈福,周少卿理
当在祈福之前将案子查清,好给圣上一个交代。”
崔仪道:“查自是要查,在徐尚书心中,您儿子比圣上金贵。”
徐竹与崔家向来不和,崔释刚直,在朝堂上便与徐竹长子针锋相对,徐台与崔仪也是从小互相看不惯,如今崔仪小小年纪便不将徐竹放在眼中,处处无礼,就如同他父亲一样令人生厌。
徐竹厌弃地抹了把泪,故作和善道:“崔世子说笑了,吾儿如何能比得上圣上千金贵体,圣上乃是真龙天子,吾儿命比草贱,自是不比崔世子,望周少卿秉公查证,切莫嫌弃草贱。”
周澍道:“徐尚书是信佛之人,佛家所言众生平等待之,子熠何故轻视草贱?此案牵扯甚广,子熠定会详查。”
徐竹长舒口气,看着儿子尸身面目全非,心中心疼悲愤,瞬间又是泣不成声。
管家问道:“周少卿,我家二郎可否由家主带回?”
周澍点头,昨夜勘验尸身,已将尸身情况尽数记下,也替徐台换了身体面衣裳,若不让徐竹带回,恐怕事情不止如此。
徐竹握着徐台的手,道:“走,阿爹带你回家。”
管家在门口招呼两个家丁进来,将徐台小心放进棺材里,棺材合上,徐竹一手搭在棺材上,一手抹泪,随着家丁抬着棺材出去,他也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