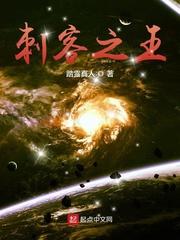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敢问偏执将军悔悟了吗 > 第59章 家人(第3页)
第59章 家人(第3页)
“奴家奴家”心下虽极为不愿,可冰冷的枪尖正抵在自己的颈脉之上,尤姬甚至可以感受到没一瞬呼吸均是擦着那见血封喉的枪尖而过。
美眸渐缓,几滴泪滴到了枪面之上,尤姬紧咬住唇瓣,终是不甘的吐出几个字,“是苏夫人。”
宋燎恩面色愈凉,他抬手将银枪在地面上蹭了蹭,直至将枪面的泪珠子蹭了个干净,这才薄唇轻启,“既知她身份,却以下犯上,这军营中竟没了个礼法不成?”
没了规矩便不成方圆,更何况是军纪严明的营地。
众人皆是被宋燎恩这句不咸不淡的话惊了个哆嗦,更有甚者直接便尿湿了裤子。
尤姬抽了抽绣鼻,顺着腥骚的气味瞥了灶头一眼,美眸中满是鄙夷。
“陈庆!”
“末将在。”
“拉出去,按理处置了吧。”
陈庆应声走进灶房,一把扯起尤姬,顾不得美人的娇喊抬手便将美人扔进了帐外的雪地中,他手握重剑,从眼尾处瞪了尤姬几记,继而眉头一蹙,粗声说道,“按理说扰乱军纪的人应当即刻诛杀,但你是营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便在此处跪到戌时再回去吧。”
陈庆乃是个粗人,平生除却沙场忠义便唯有这一个疼在心间的妹子,至此面对美人垂泪,更是不懂得怜花惜玉。
他抬首望着灰朦的天,唯恐这雪落的更大些才好。
日暮垂落,风雪愈甚,只余下一盏烛火在略显寒凉的帐中独自摇曳。
无忧妆发已卸,墨藻般青丝洒落满个小榻,此刻的她仅着了一件寝衣紧紧偎在被之中,团成了一团。
她看了看桌上的更漏,大抵是亥时了,适才同大哥几人用晚膳时还不觉冷,可边塞寒重,隆冬里小小的火盆终是抵不住渐浓的风雪。
“夫君?”
“何事?”宋燎恩端坐在圈椅中读者兵书,昏黄的烛光落在面颊之上,将他寡白的面色渡上了一层暖意。
“今日为何这般护着忧娘?”
“你是我的妾。”宋燎恩抬指将兵书翻了一页,漫不经心的回着话儿。
无忧抿抿唇瓣,思索几许后,又试探着问道,“那我们算不算一家人?”
宋燎恩呼吸稍怔,几瞬后,他将兵书放下,隔着丈余的距离,遥遥望着榻上的小女人。
但见小女人一脸真挚,湖蓝般清澈的眸子中溢着诸多的情绪,不安,疑惑,更多的是化不开的期许。
妾,于世家中讲好听些算半个主子,可实际上不过是个泄阳之物。他活于沙场,生性更是薄凉,只眼前这个小女人
宋燎恩略抬眉眼,忽然忆起无忧的身世来。自幼孤寡,讨活于市井,好容易得了个师父,被人疼惜了几年却又是孑然一身,这样跌宕的日子,却依旧是副纯真的性子也是难得。
他是个极为聪慧之人,稍加思索便知小女人对“家人”的期许,左右是想留在身边的人,同桌同榻,大抵上也是算的,于是缓声道,“算的。”
轻轻两个字却令无忧心如鼓捶,她咽咽喉咙,禁不住湿了眼眶。
半晌后,才又红扑扑着脸望向宋燎恩,满目认真的讲道,“夫君,我想同你讲个事。”
“何事?”
“既然是一家人,那我我替你生个像你我的孩儿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