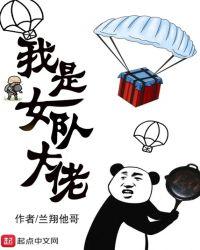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换药(第1页)
换药(第1页)
这边的陈定霖只顾着温香暖玉在怀,却丝毫不知道他前脚带了斛律云绰出来,后脚的国公府北苑,却出了大事。
事情原本也并不复杂。
经过了几日的好生将养,白氏恢复得很快,除了说话和下地依然不太利索之外,其余的表现,与一般寻常的老妪无异。
这日一早,白氏照例服药,可是不过两刻钟的时辰,还在听着陈定雯絮叨闲谈的白氏却突然翻了个白眼,继而口吐白沫,人也顺着摆好的软枕缓缓地滑了下去,接着便昏迷不醒。
陈定雯尖叫一声,急急忙忙出了内室,却对守在外室的庄令涵视而不见,直直出了卧房门,叫来了外面的黄媪。
庄令涵闻此巨变,也赶忙入了内室,一看白氏的病情急转直下,便不顾礼数,掀了白氏身上盖着的被衾,就给白氏诊起脉来。
此事并不寻常。
庄令涵自白氏发病以来便提起的一颗心,终于是稍稍稳了下来。她早就料想到有人要借白氏的病发难,但具体是谁,她尚不清楚。
这么几天以来,因为白氏的病况好转很快,她和赵太医一直沿用那个她最先开的方子。即使是白氏的身体起了变化,那方子就算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也绝无可能让白氏突然如此。
唯一的可能,只有那服下的药生了问题。
果然,白氏的脉相也是如此,只是庄令涵尚在沉吟,那黄媪领着赵太医已经赶了过来。后面并着满脸焦急的淳于氏,和竟然有一丝得意的陈定雯。
庄令涵眨了眨眼睛,希望是自己眼花,看错了。
赵太医的结论和她的一致,但追查药的问题,却有些为难。毕竟那汤药已经被白氏服下,即使去掏那残存的药渣,也未必就能真正发现问题。
白氏的病情要紧,赵太医迅速施针,先稳住了她的情况,后又带着庄令涵,身后跟着黄媪和匆匆赶来的秦媪,直奔药房而去。
几人正走到药房门口,想要入内寻找蛛丝马迹,却迎面见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妇人,正兜着一个小药筐,准备离开药房。
“站住!”秦媪不愧为国公府的大管家,光是这两声喝止,便让那妇人吓得一个哆嗦,差点端不稳手上的药筐。
那妇人连头也不敢抬,直直便跪了下去,地上还残留着这几日断断续续留下的雪水,这一跪,那妇人的膝间立刻湿了一大片。但她手里的药筐却并未落在地面,而是被她哆哆嗦嗦地端着。
“鬼鬼祟祟的,这是准备做什么?”秦媪丝毫不给那妇人好脸色。
“奴婢,奴婢见这些药材无人问津,扔了可惜,便,便想着能自己偷偷带走一点卖了换钱……”那妇人坑坑巴巴地说道,手上抖得像筛子,“奴婢第一天到药房里来当差!起了贼心,才犯下这错,秦妈妈饶命,秦妈妈饶命!”
“你叫什么?”秦媪冷冷问道,“你说你第一天到药房里当差,之前在哪里,又是谁安排你过来的?”
“奴婢姓温,原来是南苑里给六姑娘浣衣的粗使。因为奴婢的相公刚好换到北苑这边做了门子,奴婢想就近多看看奴婢的相公,好互相照拂,便给了郭媪一些好处,求郭媪将奴婢调到这药方中来当差。”
“秦妈妈,郭媪可是六姑娘的乳母,”黄媪适时插话,对秦媪没有一丝恭敬的态势,“她平日里也和六姑娘一样谨小慎微,怎么还能把手伸到药房这里来了?”
秦媪尚未答话,又听见那温姓妇人直接开口回答了黄媪的疑问:“郭媪和主管这药房的隋媪是远房表姐妹,当初这隋媪也是郭媪牵线搭桥弄进国公府当差的,这种事情,郭媪跟隋媪开口一句,隋媪便做个顺水人情罢了,并不,并不复杂。”
黄媪却嗤笑一声,对秦媪道:“国公府内各房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小小的姑娘乳母便可以随意插人到这可以榨油水的药房中来。秦妈妈,这事查清楚之后,咱们恐怕也要好好理一理那些你我不知道的暗中往来呢。”
秦媪并不接黄媪的挑衅,始终面色沉静,上手接过那温姓妇人手中的药筐,递到了略显尴尬的赵太医和庄令涵的眼前,正声道:“二位看看,这可是给老太君的汤药准备的药材?”
其实早在她们几人争执之时,庄令涵便已经仔细瞧了那药筐中的药材了,确实是给白氏熬的方子,只是有那么一两味药,看起来却有些不太寻常。
赵太医接过药筐,凑到眼前仔仔细细看了一下,然后又递给庄令涵,紧着嗓音道:“庄氏,不如你也看看?”
庄令涵见他面色不睦,心知是这药材出了问题,又细细一看,才对一直凝神静气的秦媪道:“妈妈,粗粗一看,这药里有两味药材有误。赵太医和妾所开的方子里是白芍,这里却是赤芍;方子里是石膏,这里却是知母。”
“因为这两味药材混淆,才使得主母今日的病况突然急转直下?”秦媪目光如炬。
赵太医捻了捻半白的胡须,开始耐心为在场几人解释:“白补赤泻,白收赤散。白芍能补,重在养血调经、敛阴止汗;赤芍主泻,重在清泄肝火、活血散瘀。这两味药虽然相似,但药效大不相同。还有这石膏与知母,虽同能生津止渴、清热泻火,但石膏大寒,清热泻火远优于知母,同时又能敛疮、止血,知母质润,只在生津止渴。老太君的内中风乃风痰瘀血、痹阻脉络所致,虽然换了药材不至于致命,可老太君年过花甲,经不起这样的损耗。”
白氏突然有异的原因被找到了,可也牵连出了药房的人事纰漏。这原本就是两件事,可白氏的药材被动了手脚,有作案嫌疑的人不在少数,既然同时被察觉,于是庄令涵、赵太医,并着牵连着的郭媪、隋媪和温姓妇人,都一道被“请”去了北苑正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