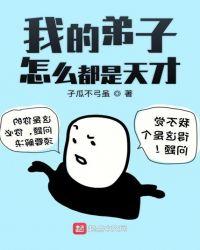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疫病(第4页)
疫病(第4页)
“将军知道,妾本是周使之妻,因为随夫来长安,才这样认识了君侯。现在,妾与妾的前夫因为君侯从中作梗,而被迫分离,妾想逃回邺城,又被君侯强行掳回。君侯对妾的所言所行,皆非妾自愿,若换做是将军,难道也会心甘情愿地,去关心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强迫自己的人?”
本来只想抱怨两句,可话一出口,便如开了闸的洪水一般。越说,庄令涵越觉得心中气恼
——可转念一想,庄令涵又自觉失语:
眼前的崔孝冲,一是身为男人,未必能真正设身处地,体会她的难处;二是,他已经习惯听命于陈定霁,自己这一番对陈定霁的“批判”,恐怕还会引起他的恼怒。
果然,崔孝冲面色变了变,她抿了抿唇,又连忙说道:“再说,君侯现在昏迷着,就算妾去看望了他,他也不会知道。”
“夫人不试试,又怎么知道结果如何?”崔孝冲的眸子里,竟然反出了窗外的雪光,“夫人的心意,君侯就算是昏迷不醒,也一定能感受到。”
崔孝冲不是没成家,甚至可能连女人都没怎么接触过吗?怎么他说出来的话,反而让她觉得暖融融的?
庄令涵突然有一些遗憾。凭着崔孝冲的才华、人品,若是不跟着陈定霁,那该多好?
“既然将军都这么说了,那妾也只能勉强,勉强一试了。”
原本还在犹豫,可是下一瞬,她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于是便匆匆辞了崔孝冲,一路去寻了陈定霁所在的西堂。
卧房门口看守的两名亲卫,是和陈定霁一并南行去抓她回来的,庄令涵认得他们。见她过来要入内看望君侯,两人对视一眼,便心照不宣地放了她入内。
里面又是无人在侧照拂,只有一个烧着的炭盆,让这一室的空旷不那么惨淡。也许,这次出来的所有宫女和太监们,□□成都已经染病。
看到炭盆,她不自觉低头又看了眼手心的伤,已经几乎痊愈了,心中不由定了定。
堪堪绕过屏风,却看见陈定霁平卧在里侧的床榻上,不似崔孝冲那般皱着眉头,平静肃穆,和他平日里看起来,几乎没什么两样。
与他相识两世,这还是庄令涵第一次见到他的睡颜。
从前,她还是他外室的时候,他来找她只为求欢,事后无论多晚,他都要离开。
如今,他每一次出现,都是那生龙活虎精神爽利的模样,她看着他此刻安静的睡颜,心中那隐隐的悸动,忽然又翻涌了上来。
她对他说过,她会将他亲手打入地狱,无论用何种方式。
现在,机会就摆在她的面前。
环顾一周,并未发现陈定霁随身的佩剑,也许在他昏迷之时,门口那两名亲卫便帮他收了起来。
她想起那日在小厢房中,他从背后抽出的那把短刀——现在,也许还放在他身上。
在右手触到他劲腰的前一刻,庄令涵突然犹豫了。
若是她就此杀了他,之后被人发现他被人杀死,那她作为少数的几个单独入过他卧房的人,自然就是最大的疑凶。
泛滥的疫病还没有真正被控制,町儿和从珠也还等着她去解救,她在此为他赔上性命,真的值得吗?
可是,她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能如此轻松地取他性命了。
过去的数个日夜,从来都是他在迫她,他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她和她在乎之人的生死,冷眼欣赏她被迫求他时低微入尘埃的姿态。
何况,无论他是否真的知情,他都是第一世害她惨死的元凶。
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把她摆在和他对等的位置,只把她视作向他讨欢的宠物,高兴了便逗上一逗,不高兴了便置之不理。
这样的他,为什么不趁着现在,彻底结果了?
想到这里,庄令涵抑住扑通扑通狂跳的心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强忍颤抖,再次将手伸向了他露在锦被之外的腰间。
他几乎合衣而卧,那短刀的位置,大约就在那里。
“枝枝……”
在碰上的一刹那,他却突然伸了手,握住她还在微颤的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