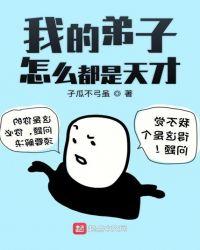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折娇枝(重生) > 疫病(第1页)
疫病(第1页)
天下憾事,往往离不开感叹“如果”两个字。
她不知道当时那国公府的人马,是否真的来了金河郡;也不知道如果来了,又是否真的将她蒙冤之事如实告知陈定霁;更不知道陈定霁知晓以后,会不会真的狠心,不论青红皂白,就要她一命偿一命。
毕竟秦媪于他,是有着特殊感情的。
而换个角度,又或者,陈定霁本人,也是真的就死在这场疫。情之中了呢?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太好了。她被他玩弄半生,最后落个凄惨收场,他这个始作俑者,却在她蒙冤离世之后不久,也“追随”她下了黄泉。
想到这里,庄令涵心中一直萦绕的苦涩不自觉淡了几分。她看着窗外的天慢慢又变浓成了黑色,眼帘也越来越重,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
再醒来时,浑身的各种不适,竟然已经神奇地消失了,只剩下饿意和渴意。
伸手给自己把了把脉,一切如常,她的疫病痊愈了!
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大约应是卯时。她挣扎着翻身下了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点点亮光,又看了看房内卧着的其他几名宫女。
似乎都没有动静。
庄令涵心中蓦地沉了下去,堵得发慌。
她慢慢走过去,一个个上去探了鼻息、摸了颈脉,可又一次次触到那冰凉至极,一次次地失望害怕。
她们都死了,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眼眶热了起来,可她已经极度缺水,连眼泪都挤不出来。她摸索着将房门打开,想要看看外面的境况究竟如何,甫一出屋子,却刚好撞到了蒋嬷嬷身上。
“庄令涵!?”待蒋嬷嬷看清来人,不禁又惊又喜,“你醒了?”
“嬷嬷,我口渴得很,可有水喝?”庄令涵抓着蒋嬷嬷的袖子,艰难地吐了几个字。
很快,蒋嬷嬷便将她带到了另一个无人的小厢房内,她一边吃着冰冷的饼,一边晃着神,与蒋嬷嬷一来一回地对话。
“太后娘娘和君侯都得了这疫病,全部都昏迷不醒,自我们从延州出发的那日算,今日是第三日了。”
“太医们如何说?”
“太医们只说是疫病,可具体什么病,究竟大家又是如何传染的,他们一概不知。这一次,有一大半的宫人和亲卫都倒下了,我听说,延州大营那边,似乎也爆发了疫病。
“金明郡这里是个小地方,在本来的计划里,太后娘娘的銮驾并不准备在此停留,故而这里的地方官也完全没有相应的准备。咱们生了病的宫女和太监,都被安置在了这里,田嬷嬷和另外两位嬷嬷也都病倒了,只有我、丹丹和其他几个,尚还算康健,但病倒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光我们两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
“太医们真的来看过我们吗?”
“唉,”说到此处,蒋嬷嬷也叹了口气,“太医们对此病束手无策,又忙着为太后娘娘和君侯延医诊治,怎么有空来管我们这些宫女?恐怕,这次除了令涵你,其他人都凶多吉少了……”
想到自己房中那几具冰凉的尸体,一股绝望之感涌上心头:两日之前,这些妙龄少女还和她一样,一起吃饭,一起就寝,偶尔互相开着玩笑,嬉闹着憧憬着对未来的向往;这才区区两日,她们有些人,便已经香魂归西,而剩下的,还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根本就看不见生的希望在何方。
想到全心全意对她的町儿,想到她拼死保下的从珠,庄令涵眼眶又热了,“嬷嬷,可知町儿在哪里?我想去看看她。”
可惜,町儿早就昏迷,庄令涵看着那个同样躺在木板床上、鹅蛋脸皱成一团的年轻女孩,心中一阵抽痛。
她还会醒吗?还会像之前那样对自己露出嘴角那两个圆圆的梨涡吗?
再看从珠,却发现她境况比町儿要好一点。
虽然也是虚弱至极,但从珠却在庄令涵为她把脉时,虚弱地睁开了眼睛。
从珠的脉相与町儿的一样,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可她再一细探,又发觉不对。
往来流利,圆滑如珠——这是,喜脉?
“令涵,原来你会看病?”从珠皱着眉头,见她神色有异,艰难地吐字,“我……我是不是,有孕了?”
“你……”庄令涵握住从珠有些枯瘦的手,心疼地说道,“你真是糊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