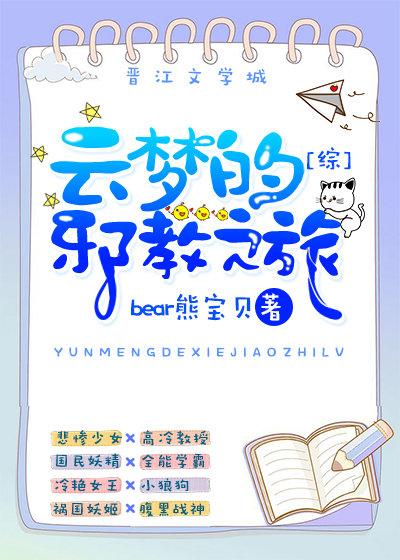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复生 > 第210章(第1页)
第210章(第1页)
明明隐瞒了那么久,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为了活下去。
但凭他的本事,足以在尸潮中杀出一条血路,何以至此!
那别的人呢?
……
孟云君答不上来,于他而言,保护同门弟子是他的责任,哪怕舍弃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他把这些小少年领出来,便理应对他们负责。
但在同样的事放到晏灵修身上时,他“舍生取义”的理智却突然不能“推己及人”了……孟云君从未有过任何一刻像现在这样,无比清晰地认识到晏灵修这番作为所带来的后果,将通过这些逃过一劫的小弟子的口,卷起一场无处可逃的风暴,注定会把他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孟云君的手指深深地刺进掌心血肉,执著地盯着晏灵修。对方似乎朝他瞥了一眼,又似乎没有,孟云君没能从他眼中窥见一丝一毫的情绪。
晴空霹雳又一次打在墓室顶,剧烈的震动回荡在整座石墓中,打断了那些义愤填膺的质问声。
这里就要塌了。
石顶开裂,透进凄厉的雷光,石头沙砾扑簌簌落下,迷得人睁不开眼。孟云君的记忆仿若断了片,怎么拉扯着晚辈,怎么从地底爬上来的这些全然没了印象,恢复意识时,他站在被碎石掩埋了的深坑边,大雪纷飞,身边早已没了小师弟的身影。
只有星星点点的热血,殷红的、浅淡的,和一行不甚明显的脚印延伸进茫茫风雪中,渐渐找不见了。
晏灵修是鬼王余孽这件事,在天枢院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即便院长三令五申不许议论,还责罚了几个明知故犯的弟子,但流言还是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毕竟晏灵修在众目睽睽之下驱使走尸自相残杀,这一事实牢牢地印在了十几个人的脑子里,是无论如何也清除不了的。
那可是控术!
过去近千年,不知有多少前辈先贤一时不慎,死在这种阴毒诡异的手段之下,又不知多少的平民百姓因此家破人亡,在昏昏噩噩的状态下父子相残、兄弟阋墙、姐妹反目……悔恨交加的眼泪、撕心裂肺的痛苦,仅仅是鬼王百无聊赖时给自己找的乐子而已。
更不要提两方彻底撕破脸皮后,在长达十余年的对峙里,那些受他驱策、悍不畏“死”的群鬼是如何前赴后继地扑过来,用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拉入混战的泥沼,哪怕明知会被打得魂飞魄散也在所不惜。
那些弱小的、无害的、好不容易能过上好日子的新生鬼们,是不是又要被再一次充作马前卒、脚下泥,好助那人成就他无上的地位?
难道以天枢院为首的驱邪师这些年东奔西走,受尽白眼也不肯放弃的理想,到此也要化为泡影了?
尽管这中间还有许多内情没有理清,还有许多疑问没有答案,那小小露了一手的“鬼王传人”是愿意静悄悄找个地方猫着还是致力于祸乱天下,这都不能阻止知情人心中的恐惧山呼海啸般蔓延开来……他们当然尚未给晏灵修定罪,可一旦起了疑心,那离罪名落实也不差什么了。
院长几次申饬,强行把流言蜚语压在天枢院内部,不让外传。做完这些后他就病倒了,但连这他也不敢表示出来,生怕别人知道了,再给小弟子添上一重“不孝”的罪名。
不说私心偏袒的院长,就是闻讯赶来的尚裾和曲临逸都不相信小师弟会是那劳什子传人。
当年鬼王伏诛时,他不过五岁大,亲朋故旧都死光了,从小长在天枢院,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怎么可能是鬼王余孽呢!
然而仅靠他们几张嘴,堵不住悠悠众口,尚裾和曲临逸忧心忡忡地在天枢院停了一晚,就马不停蹄地离山去找小师弟去了,还要去个别已经听到风声的门派,求他们手下留情,待天枢院查明真相后再做定夺。
孟云君走不得……他是天枢院的大师兄,又亲眼目睹了晏灵修使用控术,必须留下来安抚人心,一连三天都忙得分身乏术。等到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何宁抱着黑猫找了过来,一见到他,先委委屈屈地扯着他的袖子哭了一场。
“大师伯,他们都说我师父犯了错,是内奸,他要是不死,全师门的清白就要被毁了。”
何宁自小就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姑娘,在以前,她似乎知道自己是可以放肆的,但凡受了委屈,必要张大嘴巴仰天哭嚎,干打雷不下雨,脸上毫无湿意,但这会儿她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只是睁着眼睛看着他,豆大的泪滴不住地顺着脸颊滑下来,开口说话时才能听出些微抽噎的气音,哀求道:“你去和他们说说好不好,我师父不是这样的人……”
但孟云君没有回答。
他没日没夜地忙碌,眼下积了一片醒目的青黑,神情也有些恍惚,听见何宁的哀求,他似乎怔怔地走起了神,不知在想些什么,直到何宁不安地喊了他一声,他才反应过来,一言不发地抬起手按在女孩的头上,抚了抚她柔软的发丝。
这几天,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孟云君一闭上眼睛,那天墓室里发生的场景就会片刻不停地浮现在他脑海。离奇的是,他所有的情绪——那些茫然无措,无奈悔恨,都如同蒙上了一层厚实的窗纸,被丢在了那个填满了随时和残尸的废墟之中,看不清也摸不着,暗流似的徘徊在他浅浅的胸口。
他没有再去纠结晏灵修在划开自己手腕时是什么心情,也不想探究这背后究竟有没有鬼王的手笔,只是殚精竭虑将这件事的影响限制一个尽量小的范围,并在每一个能抓到的空隙反复推演思量,该用哪个理由保住晏灵修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