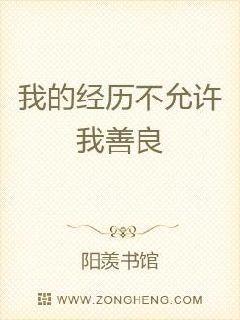墨澜小说>被宿敌推下断崖以后 > 第150章(第1页)
第150章(第1页)
“你活不久了,是么?”
云罕攥了一下手指。
“你想和他们同归于尽?”宋庭誉继续说。
“你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因为这是最后一面了,所以……你打算永远都不告诉他,是不是?”
云罕终于恢复动作,对这汹涌而来的几个问题一个都没有回答,甚至没有回过头。
他只淡淡说了一句话,带了些笑意,零碎、低哑……飘零在风中。
“您会尊重我的选择罢?”
“宋将军。”
无论发生什么,结果如何,都该由我自行承担。
宋庭誉不再吱声了。
……
水牢的门打开,又窜一阵阴风,云罕在这阴冷潮湿之所待了片刻,眼前有些发花,刚出门就一个趔趄。
“……”
手臂被人撑住,他略显涣散的瞳孔向上望去,正看见薛界欲言又止的薄唇。
“都办妥了,先回去。”他借着对方的力撑起身,扫了一眼周边,被烈酒放倒的守卫东倒西歪地倒在桌面上。
二人一直走到一处里屋,确认屋外无人后,方关上了门。
云罕虚浮的身体在这一刹那“轰通”摔到了地上。
薛界骤然转首,唤了他一声,得来对方的摇头,迟凝片刻,一把将他抱起来放到榻上。
“……你去哪儿?”云罕撑起眼皮,看见对方沉默转身的背影。
“煎药。”薛界顿住脚步,面具加持下的脸色看不出神色。
“不用了,我休息一会儿便好。”云罕摇了摇头,虚虚掩掩地闭上了眼睛,“蒋国安不会相信你的身份,你且留在这里,最近几日是至关之际。”
薛界被他的话滞留在了原地,手指慢慢攥紧。
屋外冷风呼啸,凛冬未尽,愈演愈烈。
身后传来低低哑哑的闷咳。
他终是转身,几步上前,将被褥严实盖到了云罕的身上。
后者半混沌时模糊睁眼,没有反应过来他在做什么,只无意对上了他的眼神,略微迟愣,“……你也不必担心宋将军,他很快就安全了。”
薛界收回了手,没有说话。
云罕没有忍受住,又闭上了眼睛,身体细微地蜷缩着,偶尔溢出一声呻吟。
没人知道他正在遭受着怎样的痛苦。
甚至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身上究竟有多少奇杂病症。
这些病症一齐发作,总会将他折磨地生不如死。
不过他除非到完全失去意识,从来都不会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
“你为什么变了。”恍惚间,意识要完全消匿时,耳边传来了一道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