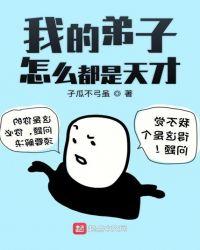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病娇厂督的小宫女 > 第98章 他的承诺(第2页)
第98章 他的承诺(第2页)
见喜被他凉凉的指尖碰得一颤,杏目圆瞪道:“气到不想吃!”
他指尖滑下去,一面柔抚,一面漫声笑道:“看来我比饭重要一些。”
她耳廓红了一片,身子在他的带领下微微弓起,颤栗到出了一层薄汗,咬咬唇硬着头皮说:“也不见得!那个……府上的厨子做饭也很好吃的,你再晚来几日,我就,我就——”
倏忽,身上有冰凉的湿意传来,仿若枝上寒露啪嗒滴落心口,一滴就是一颤,带着酥痒的凉意从毛孔渗入骨血,四肢百骸都沾染了他的气息。
她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想说的话吞咽在喉咙里,双腿屈着无所适从,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用未受伤的一只手与她左手十指相扣,将彼此的温度深深熨帖在一处。
他的侧脸,有淡淡的光影,和轻轻跳动着的、她的影子。
寒风将光影吹散,檐角的冰凌在纱灯摇曳的火苗下,闪动着明黄而晶莹的色彩,仿佛下一刻就要融化,却又迟迟不化。
最后她累得不行了,眼里浸着湿意,枕在他月匈口沉沉欲睡,轻而低的喘息声是这世上最温柔的乐章。
……
养心殿,青烟淡淡。
王青躬身进来,面露为难之色,想了想还是上前揖道:“坤宁宫皇后娘娘闹绝食,已经是第二日了,说一定要见您,陛下……打算如何处置?”
赵熠眉头蹙紧,沉吟半晌,搁下手里的奏本,起身披一件明黄大氅,与王青一同往坤宁宫去。
夜色极深,天上无星无月,夜幕笼罩下的紫禁城冰寒彻骨。
坤宁宫,住过先太后,如今住着他的皇后。
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记得请清清楚楚。
他淡淡扫过去,一些幼时的记忆翻涌上来,若在以往,那些刺耳的言语就像冰刀一样在心印刻捻磨,可今日,他的面色平静得出奇。
缓缓走上短短一截汉白玉石阶,从廊下入内,坤宁宫也早已失了往日的脂粉味道,掠过鼻尖的只有淡淡的炭火味。
紫檀木卷草纹案几上的琉璃瓶内,是一株边角不再脆嫩的红梅,在烛火的阴影下显出颓然的气色。
寒风席卷进大殿,皇后跪坐在妆奁前,昔日一双秀目仿佛腥臭的死水深渊,激不起一丝波澜。
一道明黄的光线打在镜面,仿若深渊落下一颗石子,终于有了一星半点的反应。
转过身来,望着面前熟悉的人脸,只觉得遥远而又陌生。
“皇帝哥哥……皇帝哥哥……”
她低声呢喃着,忽然发疯似的扑到他面前,双手抓着他臂袖上的日月纹,三足金乌在尖利的指甲下,皱起深深的褶子。
她已不知道自己的嗓音比扼住脖子的老鸹还要沙哑,双目里蜿蜒着无数的血丝,与往日的明丽光线判若两人。
赵熠眸光深邃冷冽,棱角分明,尤其是面色夷然的时候,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她深深望着眼前人,兴许是知道得太晚了,还总以为他是幼时那个孱弱可欺、事事听话的少年。
再不济,也是任由她在后宫作威作福,却还不得不哄着她的皇帝哥哥。
可惜不是,都不是……他是一道圣旨亲手将他的父亲打入大牢,正在午门斩首和凌迟处死之间举棋不定的天子,是欲将她抄家灭门,将整个张家打入无间地狱的帝王。
她眼眶涩到极致,已经流不出眼泪,“皇帝哥哥,我爹爹不会私藏印信的,他不会谋反的,更不会陷害任何人,是梁寒,一定是梁寒……”
赵熠眸中透着说不清的情绪,仿佛倨傲中透着淡淡的怜悯,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张婵不死心,咬咬唇又急声道:“你去查清楚,去查清楚啊!一定是梁寒诬陷他,才找出这么荒唐的证据来!”
赵熠许久未语,眼底已流露出厌恶之情,半晌才冷声开口:“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张婵眼睫跳了跳,失魂落魄地摸到自己的小腹,那里依旧很平坦,彩缨说是她不曾好好补身子的缘故,所以没有像普通孕妇般微微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