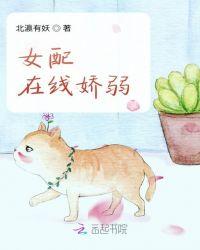墨澜小说>二手情书 > 21沈问秋转过身毫不犹豫地 (第2页)
21沈问秋转过身毫不犹豫地 (第2页)
他现在前所未有的后悔。
他为什么要一直牢记陆庸的电话?他为什么要让警察给陆庸打电话?他为什么不拒绝陆庸来的收留?他为什么要赖着不走?
陆庸究竟是怎样看待他?他到底为什么要回到陆庸面前?假如不出现,陆庸就不会发现他变成这样。
还不如不声不响地去死了,起码在陆庸的回忆里,他还能保留一个最后的美好形象。陆庸对以前那个干净的他有几分余温未尽的喜欢,就对现在的他有多失望吧?连他自己都这么厌恶自己,谁会喜欢他啊?
沈问秋跑进了附近的一座公园。
他以前经常在这里遛狗,也在这里记不清有多少次牵着奶糕跟陆庸一起散步,谈天说笑。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胸口疯涨的痛苦抑郁情绪将其他所有感觉都压住,跑着跑着,跑到公园的尽头,跑上一座大桥,跑到实在跑不动了,喘不上气,才停下来。
双腿肌肉发抖,连站都快站不住,沈问秋按着胸口,慢慢地蹲下去,视线模糊的看着水泥地面,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坠落在尘埃里,洇出一个个小圆点。
他跪在地上,生理和心理都在反胃,不停地咳嗽和干呕。
想把自己脏污的灵魂给吐出来。可是不行。
一双棕黑色的方头男士皮鞋出现在他低下的视野中,沈问秋顺着往上看,目光只停在笔直的裤管边,看到那双粗糙宽厚的手掌,不必再自取其辱地抬头。
“沈问秋。你站起来。”陆庸说,“我不扶你,你自己站起来。”
过了好几分钟,沈问秋才手撑着地,发抖地从地上爬起,站着,但站得不直,也站得不稳,像是随时会倒下去。
江风很大。
沈问秋感觉自己被吹得摇晃,没什么力气,他只站了一会儿,不管陆庸的话,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乞丐一样,仰视着陆庸。
他已经没有退路,没地方可躲了,躯壳像被掏空,麻木而平静地直视陆庸,嘴巴和声带自顾自动起来,以他能做到的最恶毒的语气说:“你他妈就非得要来看我的笑话吗?我不是都给你留了纸条让你别找我了吗?算我求了你了,大哥,你为什么这么阴魂不散啊?因为我问你借了钱吗?就那么几千块,你当做慈善好了,你在乎那点钱吗?”
陆庸昨天开车那么久,一下车又被拉去赌场,再从警察局出来,二十几个小时没合过眼,眼睛发红地紧盯着沈问秋。沈问秋这番自私刻薄的话如一把尖刀,直刺他心口,鲜血淋漓。
揭开了伪装的面具,难道这才是沈问秋如今最真实的模样吗?这个尖酸无赖、浑身戾气、不再年轻的男人。
陆庸:“你想做什么?”
沈问秋:“关你什么事?你是我什么人?你忘了我们绝交十年了吗?”
陆庸:“我担心你……”
沈问秋:“我让你担心了吗?你别以为收留了我几天,就有资格管我了。管得真宽。他妈的,麻烦死了。你还有脸说什么担心我,你把老子害惨了好吗?你不是真打算去赌,你跟我说啊!我报了警把他们全得罪了,这下我是真的完了。”
陆庸心急如焚,偏偏说不过他,张了张嘴,恼火至极却想不出该怎么接话。明明沈问秋就在他面前,没有动,可他就是有种沈问秋在远去的幻觉,让他下意识地往前逼近。
沈问秋亦有一种会被抓住的感觉,叫他不由地心慌急躁,他猛然站起来,使出浑身力气推开陆庸。但陆庸长得比他高大强壮太多了,像一座铁塔似的,他根本推不动:“你滚开啊!我让你滚啊!!”
“你他妈的神经病啊?!!!”
陆庸闷声说:“小咩,你冷静点,你冷静一下,我带你回去。”
沈问秋听到这个称呼,彻底崩溃了,心中最后一根弦也断了,眼泪瞬间如决堤般疯狂涌出来:“恶心不恶心啊?‘小咩’?害‘小咩’呢?那他妈的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陆庸,你到底对十年前的我有多么念念不忘啊?别傻逼了!你他妈的睁开眼看看我现在有多烂!我跟‘小咩’就不是一个人!”
陆庸不说话了,像是谁都不能撬开他的嘴。
沈问秋瞪着他,安静地落泪,落完泪,复又平静下来。
沈问秋就觉得自己傻,真的傻,难怪落到今天这步。陆庸是在对他好吗?陆庸是在透过他,对十年前的他好。他也喜欢十年前的自己,谁会不喜欢呢?
可最让他痛苦的就是时光永远不可能倒流,他回不去了。
他还想不给陆庸添麻烦,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怕死而已,真懦弱啊,都要死了,死后一了百了,哪管得了身后的事?
陆庸僵着脸,近乎执拗地说:“我不那么认为。你是沈问秋,沈问秋就是沈问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