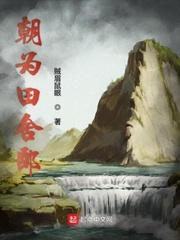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应许如是 > 秦广王引魂郎(第1页)
秦广王引魂郎(第1页)
塞北林莽,黄云白草,魂幡卷扬,易家新丧。
易仲良不过一个得过且过的文官,老实本分,无心名利,不曾卷入任何朝堂纷争,他不明白自己何时得罪过眼前这位镇北杀神,爱女将将入土,他就要掘墓开棺,实是悖逆乱常。
“纪北睦,你说什么!”
“开棺。”
易仲良脸上新旧泪水被风干,皮肤发紧发涩,他抹了把脸,侧头看看不远处几匹北军骑兵特有的墨色战马,盔甲上是寒露凝结的白霜。若他没有记错,关内侯、车骑将军纪淮所率北军应该在沥县扎营,距此快马也要三四个时辰。
“你赶夜路,就是为了……刨小女的坟?”
纪淮默然,话虽难听,但确是事实。
他的沉默在易仲良看来简直是莫大羞辱:“纪北睦!即便是我不知何时何处得罪了阁下,得饶人处且饶人!罪不至惊扰亡灵吧!”
纪淮面色没有比易仲良好看到哪里去,他张了张嘴,却没有吐出半个字,索性挥挥手,不远处静候的亲卫得到指示近前,纷纷跳入坑中,拂去棺椁上沙土,合力推开石椁。
原本雁门郡郡守府的兵仆还想要上前阻止,但见纪淮左右副将抽刀撬镇钉,刀光寒,威慑凛,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妄动。
纪淮杀名惮赫千里,一杆昆仑槊点地,十万匈奴颤胆,他若执意要行逞凶肆虐之事,怕是武宁帝在也会偏袒,小小郡守府哪是对手。
易仲良新妇紧抱女儿生前最爱的木枕,似认命般颓然倒地,几欲昏死,颜色比棺中亡女还要差些。
“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话都不曾说过半句……纪北睦,纵然你权势滔天,也不能仗势欺人,如此作践易家……”
纪淮跳入坑中,正要推开棺盖,听得易仲良如此说,转身撩袍跪下,拱手道:“纪淮并非有意欺辱,开棺此举自知冒犯,但不得不尔。之后易郡守如何泄愤,哪怕生杀活剐,纪淮绝无二话!”
他红了眼眶,音色一半是在所不惜的决绝,另一半,是近乎声气相求的哀鸣。
易仲良不知所谓,指着纪淮“你你你你”半天。
纪淮不再多言,起身推棺。
新鲜空气重新注入,对流之下棺内扬起一阵风,裹着仲春时节塞北草原的余寒四散而去。棺材里身着敛服的尸体猛然睁开双眼,腾地一下坐起,贪婪将冷空气吸到肺底,而后呛地直咳。
冷风醒神,周围一些胆小的仆从妇人反应过来,嚎叫着四散逃去。易仲良僵在原地,易夫人怀中木枕哐啷啷跌落。
武宁十一年仲春,雁回瀚海,魂归此岸。易生缠绵病榻十一年,向死而生。
她紧紧扒住棺材邦子,惊恐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身边束镂空蝠纹冠,着罗纹玄金甲的人身上。
这人通身威厉浩气,五官隐约见少年飒爽,更多的是饱饮风霜的世故,他亦被吓一跳,宽厚双肩一抖,墨色瞳孔剧烈收缩。
易生抓起掉落身旁的玉琀,气急败坏扔出去:“什么玩意儿差点噎死我!人死没死透你们都不做最后检查核对吗?上来就活埋……你们负责人是谁?我要打市长热线投诉你们儿戏生死!而且!土葬犯法知道吗?!”
她还在絮叨,忽觉腰间一紧,她被身旁人打横抱起。那人抓着她单薄的肩头,在她脸上细细看过,便紧紧摁在怀里。
易生的脸蹭过他浅浅胡渣,刺痛刚起,眼底又被勒的充血发胀,脸色瞬间从苍白变成朱紫色,她被迫紧贴他的脖子,甚至能清晰听见对方血管上传来强劲心跳。
好家伙,殡仪馆都是这样补救工作漏洞的啊……
易生心中暗惊,求生的本能让她迸发出巨大力量,她疯狂挥舞双手,又捶又打,待那人稍微松开力道,她便趁机借着腿劲蹬翻在地,重重砸落在精美的金银铜器上。
头晕目眩,说不准是摔的,还是被金银闪到的。易生心中大骂,她连轴加班,拿命换来的钱居然被他们大办奢华丧葬,这不是吃绝户是什么!
此时不宜多思,逃命要紧。她手脚并用,龇牙咧嘴的往坑上爬。
爬到一半,腿还挂在坑沿上,四周原野风光,和浩浩荡荡素车白马就将她镇住。十几个男女身着麻布葛衣,分工明确,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瘫坐在地上,惊骇之下慢慢捂住自己的嘴,情绪饱满,层次分明,十分专业。
易生顿时怒极,咬牙道:“我的葬礼,你们沉浸式体验是吧?还找这么多NPC?真是有道道来霍霍我的钱!”
她瞅准站在最前面一女子的脚腕,伸手抓住借力翻上地面。那女子本就被吓的动弹不得,被这一抓更是过度惊恐,直接闷声倒地,昏死过去。
随着她一倒,剩下那十几个男女尖叫着“诈尸啊”鸟兽散。
易生骂骂咧咧爬起,刚逃两步就觉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又勉强逃了两步,便两眼一黑,直直倒下,伴随那对中年夫妇的惊呼,她跌进一个肌若金石的臂弯中。感官彻底消失前,她似乎闻到淡淡不知名清香,夹杂金属腥气。
待易仲良夫妇安顿好易生,想要找纪淮问个清楚,却得知他早已连夜又赶回了沥县。这下夫妇俩更加茫无头绪,惴惴不安起来。他是来挖坟掘墓的,却在事后无甚纠缠,悄无声息离开。
“他又改变主意了呗!”易夫人李竹君替昏睡不醒的易生掖好被角,漫不经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