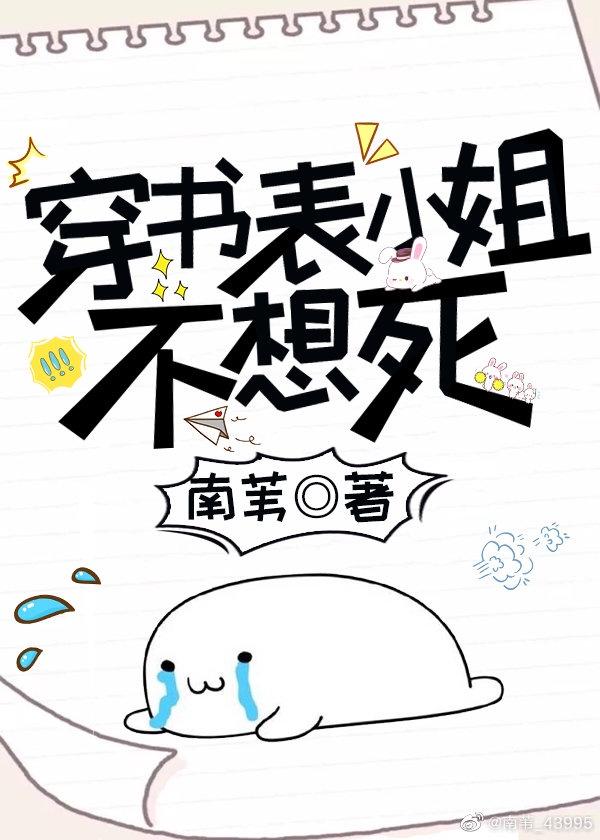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时空调律者 > 第十二章 地心游记九(第1页)
第十二章 地心游记九(第1页)
“等等!”大保罗突然挺直腰板,萎靡神情一扫而光。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神甫面前,视线仿佛尖刀,凶狠地剜向对方:
“‘最初井’边上?‘克里斯托弗’?这是什么见鬼的名字!告诉我,那具尸体看着是啥模样。神甫,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现在就告诉我!”
“你忘了说‘请’。”埃米尔潘一面嘟囔,一面踉跄地向洞壁退去。不过,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抓住别人的用词大作文章,扶墙站稳以后,便开始迫不及待地回答问题:
“克里斯托弗只是代号,我按a、b、c、d的顺序随意取的。至于特征,那具尸体确实有很多奇怪特征。比如说,明明地底如此潮湿,它却干瘪的只剩皮包骨头。还有衣服,尸体穿着的衣服。那不是什么贵族华服,只是普通的亚麻套头衫,又破又烂还是单层布料,但颜色挺浮夸,褪色前应该是绛红。”
“绛红。”大保罗伸出双手,像是要攥住神甫脖子,脸上血色全无,嘴唇就像害病似地剧烈颤抖:
“该诅咒的绛红!神甫,他脑袋长什么样?我的意思是后脑勺,后脑勺是不是扁的?左腿,对了还有左腿,那上面有没有剑伤?大腿外侧很长一条,差一点就能碰到膝盖。别急,我还没说完,你干吗这么着急?獠牙,脖子上有没有戴着一颗獠牙,绿肤兽人的獠牙?那是他爹从战场上得来的,被他一直当成宝贝。神甫,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冷静,冷静!”埃米尔潘被逼得一躲再躲,神情变得极其狼狈。他甚至把脑袋转向弗朗辛,不断地眨眼求助,但女性雇主却对此毫无反映,就好像根本没看见一样。见求援失败,驻村神甫只好把整个人贴上洞壁,一面忍受头顶落下的水滴,一面努力拼凑词句,好应付咄咄逼人的大保罗:
“让我仔细想想。别催了,让我再看看笔记!我当时——我当时——找到了。后脑勺确实是扁的,和你的描述一致。剑伤什么的,当时没有仔细看。兽人牙,兽人獠牙我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你别着急!尸体确实戴着某种装饰品,但我们当时只有火把照明,而且着急赶路,所以——冷静,士兵,冷静!你就算再逼迫,我也无法提供更多信息了!”
“抱歉。抱歉。”大保罗喃喃自语着,从神甫的衣领松开双手。他低下脑袋,看着从科特韦梅勒一路穿来的牛皮靴,堪比狮子的凶狠眼神,迅速黯淡下来。“光问问题没用。确实没用。必须实地看看,必须到那边实地看看。阁下,索仲武阁下!”
“在。”索仲武早就停止了脚步。他向弗朗辛点点头,随后便掉转动力装甲,与突然雄起的大保罗对视起来:
“我们肯定会检查‘最初井’,这个不必担心。保罗先生,那具尸体,是你认识的人么?需要帮忙的话,只管说。”
“我确实需要帮忙。如果他还躺在那里的话。”大保罗攥起拳头,肩膀不住颤抖,声音带上了哽咽:
“二十三年。二十三年。真没想到,居然还有机会见到他。巴雷!巴雷!!我回来了,我回来帮你了!”
声声惨呼,仿佛受伤野兽发出的悲鸣。小阿尔贝默默地走向老兵,以极其微小的力道拉住对方胳膊。“保罗大叔。”他仰起脑袋,脸上全是担心:
“他是你朋友吗?很好的朋友?”
“是我表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大保罗把脸转到一边,应该是在遮掩表情:
“那天,我们忍着宿醉,把第一层转了个遍,结果连逃犯的头发都没瞧见。什长可能是想逞英雄,非要从‘最初井’下去,到洞穴二层碰运气。如果当时有老兵跟着,肯定会出手阻止,但一起进洞的八个人,最大的也就十九。总而言之,当时谁也不愿意当胆小鬼,队长拿话一激,我们立刻把绳子绑在腰上,咋咋呼呼就下去了。”
“数千年来,凡人始终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弗朗辛发了句感慨,同时迈动腿部单元,示意“远征军”继续前进:
“然后呢,保罗先生?你们是马上就遇到了怪事,还是隔了很久以后?”
“也没隔太久。”大保罗揉揉小阿尔贝的头毛,开始与男孩并肩而行,情绪似乎有所平复:
“我们在地洞二层,只待了不到半个小时。那地方实在太黑,火把只能照出几尺远,和一层完全不是一回事。大概从第十分钟开始,怪事便开始接连出现,我们越走越担心,越担心,周围就越不对劲。先是头顶上呼啦啦传来水声,问题是附近根本没有地下河;没过多久,又有女人的哭声飘过来,我当时听得清清楚楚清楚,但巴雷他们却一直说听不见。”
“很像恐怖片桥段。”索仲武忍不住评论了一句。他必须一面走路,一面关注四旋翼传来的影像,同时还得操心无人车绘制的地图,可以说片刻不得闲。但大保罗讲述的往事,却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不知不觉就把他的心思勾了过去,无论如何都想参与谈话:
“接下来,是不是有人突然走散,而且一句话也没留下?”
“你猜的很对,索仲武阁下。稍等。”大保罗低下脑袋,用法语方言对小阿尔贝讲了很长一段话,这才把笠盔重新抬起:
“失踪的是达尼埃尔。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啥时候不见的。队长有事要吩咐,连喊三声也不见答应。弟兄们赶紧点着提灯,在洞里转了七八圈,结果却只找到几片蜘蛛网。然后,巴雷他,巴雷他就——这家伙,为啥那么好心!”
“每到危急时刻,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接话茬大师埃米尔潘,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实力。不过,他这回没有阴阳怪气,而是一本正经地掏出玫瑰念珠,干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