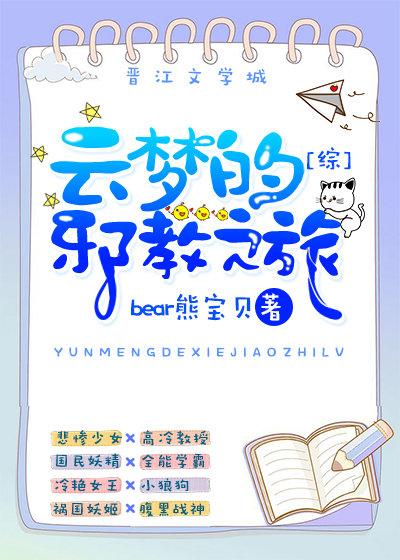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千岁爷的掌中小娇医 > 第五十五章 少管少问(第1页)
第五十五章 少管少问(第1页)
韩朔骂完,心里畅快了些,后怕就涌上来了,眼睛一瞪,指着宋祁言道:“你今儿不是娶亲吗?”
“手下怠慢,本督给馆主赔礼了。”
宋祁言没答他,引着他到寝房,“请馆主费心看看。”
煞神给他道歉,韩朔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望向拉着床帘的红木雕花大床,不由好奇里面躺着何人,能让煞神纡尊降贵,连洞房花烛都不顾了。
“馆主,救救郡主!”
郡主?掀开床帘,韩朔呆了下,“丫头?怎么这样了?”
不紧不慢地态度微变,话音染上急色,不用宋祁言催,双指并着搭上虞青然的脉。
床边几人看他一会皱眉一会叹气,心都急到嗓子眼了,好一会,韩朔收回手,抚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了宋祁言一眼。
“馆主,如何?”茯苓急道。
“郡主这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最重要的是,这心病乃需心药……”
韩朔叹道,问茯苓:“你家郡主近些日子是否郁郁寡欢?”
茯苓点点头,眼睛微红,“郡主先是被禁足,接着将军又出征,还有……”
顿了顿,茯苓看了眼宋祁言,转了话头:“可能郡主不愿叫我发现,我只常常见到郡主枯坐发呆,我想郡主是担心将军……”
“仔细调养倒也不是大病。”
飞栾取了笔墨,韩朔写下药方,想到什么,又道:“哎,说起来那丫头的母亲也是心病去的。当时将军不在上京,写信托老夫去看诊。”
言
及此,韩朔面上浮现怅然,“当时她的郁病谈不上太严重,用老夫的药方调养数月应该能见起色,怎料却突然恶化,撒手人寰。”
佳人早逝,韩朔叹息:“可见这心病,药石治标不治本。”
昏昏沉沉中,“郁病”“药方”几个词钻入耳朵,虞青然脑子一疼,下意识想抓住什么。
茯苓就在身边,看到虞青然不安的手,急问道:“郡主,郡主怎么了?”
眼皮好似有千斤重,虞青然想睁开眼,忽然一只大手盖在脸上,那手很暖,骨节分明,很有安全感。
“有什么事待会不能说?”
低醇的声音循循善诱,“先顾好自己身体。”
疲惫的身体叫嚣着罢工,舒服熟悉的气息在侧,虞青然僵持的神经微松,深睡过去。
看着宋祁言覆在虞青然脸上的手,这举动似乎太过亲昵了,茯苓蹙眉,宋祁言是宦官,以前她不曾多注意,可是宦官也娶亲了,就该当成男人看待。
郡主快要及笄,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
时辰不早,韩朔看着虞青然服下药,便告辞了。
与此同时,督府宾客满座,喜气洋洋。
朝中官员来了近半,重云几个忙着招待,寂雨一身新郎服,手举酒盏,走过各个酒桌。
宋祁言没在,他被灌了许多酒,脚步沉沉,视线模糊,重云无语地扶过他,见时辰差不多,示意几个侍从去前院待客。
“重云,我容易吗我!”
寂雨一开口就打了个酒嗝,
重云嫌弃地退开,“臭死了。”
寂雨更忧伤了,趁着宋祁言不在,大肆抱怨道:“你说有这样的吗?今儿酒桌上我承受了多少?这到底是主子娶亲还是我娶亲啊!”
斥责的话就在嘴边,看他醉红的脸,重云无奈耸肩,罢了,跟醉鬼讲道理就是白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