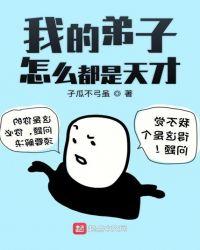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正好是你 > 第 14 章(第1页)
第 14 章(第1页)
了一锅酸菜米线,又烤了小豆腐端上来。秦峰把这个项目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大概就是为某个县城的文化建设做个宣传片,要涵盖经济、民生、教育等方面。县城在深山里,附属的一些村镇曾是明代的军屯,有古老的民居还有很丰富的考古收获。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默记。米线也很好吃,我把汤全部喝完了。
这中间秦峰接了很多电话,都是他老婆打来的,有几次他不得不走到离我远一些的地方去接,后来他干脆就不回来继续吃了,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我回房间洗漱收拾,敷着面膜去走廊里透透气,秦峰还坐在天井的花坛边上打着电话。手机电池可真扛用。
对照着秦峰给我的一大堆资料,我把紧接着两天的拍摄提纲粗略写了一下,做了简单的拍摄安排。次日一大早,秦峰开着车载着我和王霄啸去了距离丽江一百公里的山里,因为是山路,所以尽管只有一百公里,绕来绕去开了大概十个小时。秦峰又开始打电话,跟老婆汇报行程。我在车里打盹儿,醒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车子停在镇政府的招待所外,王霄啸说:“姐们儿,你知不知道你一路鼾声如雷。”我平时从不打鼾,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骗我。
那些天我就跟王霄啸四处拍摄,秦峰干脆不出现了,大概还是在跟老婆煲电话粥吧,反正他只要安排好我跟王霄啸的行程食宿就行,他要在我还不自在呢。晚上我们拿着存储卡去他房间导素材,顺便让他也看看每天的拍摄成果,查漏补缺,他挺好说话,不事儿,不过每天满脸疲态,眼睛发乌,我忍不住问:“秦哥你是不是没休息好,黑眼圈这么重。”
他使劲揉揉眼睛:“哪里呀,我精神好着呢!”我觉得他的眼圈越揉越黑了。
意外发生在拍摄的第七天。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遭遇了。
那天我们正在县文化所采访所长,一栋五层水泥小楼,所长带我们去一间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里看前些日子从古墓里发掘的物品。有碎裂的瓷罐(据说是用来装骨灰)、陶器、木雕,我小心越过地上的一个个大麻袋,拿着话筒问:“这麻袋里是什么啊?”
所长弯下身子(王霄啸的镜头跟着他)说:“哦,这里面全是墓葬里的骨殖,散的,我们用麻袋装起来了。”
我一抖,差点扑倒在一个麻袋上。
秦峰鬼哭狼嚎的声音断断续续从外头传进来:“江唐,江唐!江唐,你快出来!”
我让王霄啸继续拍,然后走到走廊上,从栏杆外探出半个身子:“嚎什么呀?!”
秦峰站在楼下朝我挥手:“不拍了!不拍了!赶紧走!”
“什么?!开什么玩笑!”
“我,我老婆说,我,我跟你有一腿,她误会了,很生气,她在地方上有势力,说要打死你,人都已经攒起来了,正在来的路上。你,你赶紧走!赶紧走!”
“我跟你都不熟!”我几乎怀疑他在开低级玩笑,“怎么可能跟你有一腿!”
“他们的人真的快来了,你赶紧走!我找个司机送你!再不走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我快哭了出来:“那拍片子的报酬呢?!”
“我现在就给!你快下来!”
我下楼去,秦峰把我放在招待所的背包塞给我,我的证件在里头,他又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万块钱,对不住,没拍完,所以不是之前说好的数。我给你买了机票,晚上九点飞昆明。你现在直接去丽江机场。”
王霄啸早觉得不对劲,跟着跑了下来:“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哭着说:“他老婆找人要来杀我。”
“真的假的,这么刺激!”
秦峰脸似苦瓜:“我老婆在公安局认识人,你在昆明住旅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别让她查出来你住在哪儿!”
“你拉倒吧!”我哭骂,“上哪个宾馆去公安都能查出来!”电光石火间我突然想起了陆坤,我擦了擦眼泪,定定神,正要把信封揣进兜里时,王霄啸说:“哎哎哎,那我那份呢?”
我把信封打开看了看,从里面抽了一沓,把一万块给了王霄啸:“行,关键时刻,你就知道钱!”我心中无比悲凉,虽然我承认我自己在关键时刻也还是惦记着钱,但我也意识到在这里没人爱我,连友爱也不够分量,因而分外伤心。
司机老张在山路上飙着车,用七个小时把我送到了丽江机场,我滴水未进粒米未沾,绷紧了神经,一上飞机就吐了。
十点半,我在昆明机场给陆坤打了个电话,他好像很吃惊,毕竟我跟他不是那种深夜打电话聊天的关系。他的职业本能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