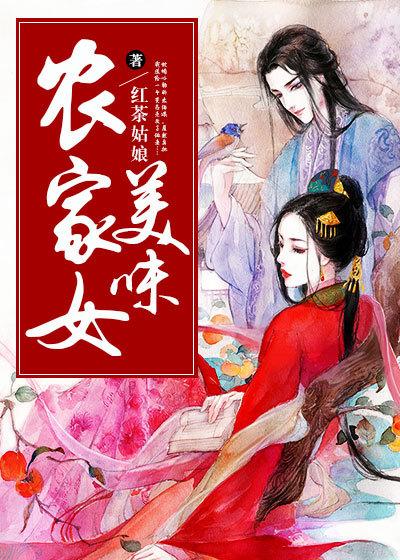墨澜小说>女帝 > 第209章 第 209 章(第2页)
第209章 第 209 章(第2页)
管家忙伺候阮权往夫人住的主院去。
“父亲。”威北侯夫人正边陪着母亲说话边等着,终于在入夜时分等到了父亲大人。
阮权颔首,在主位坐下,才问:“今日怎么回娘家来了?”
威北侯夫人看了看母亲,又扫了一眼屋中伺候的仆役,对父亲笑道:“许久不曾回家来,女儿十分思念父亲母亲。”
阮权威严训女:“你已出嫁多年,许多话不需要为父说也都明白,你夫君不在京中,你更要侍奉好舅姑,为你夫君照顾好家中。”
大梁惯例,武将领兵在外,家眷必须留在京中。威北侯傅启丰在节度戎州,他的正妻阮氏定然是不能跟去任上必须留京的。
“女儿谨遵父亲教诲。”威北侯夫人站起来福了一福,随后坐下,再扫了仆役一圈,对阮权道:“父亲,女儿今日回家,还有一事,是为人所托。”
阮权明了,挥手让伺候的人都下去,待仆役都退下了门关上了,他才道:“什么事,是吧。”
威北侯夫人说:“女儿是受了蔺姐姐的托,转告姚世伯的话给父亲。”
阮权皱眉。
“姚世伯道,想问一句,父亲想不想坐上枢相的位置。”
阮权猛然一惊,下意识斥责:“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威北侯夫人无端被斥责了也没有心生不悦,声音轻轻柔柔地说:“父亲在枢副的位置上多年,蒋相公入狱亦多年,父亲一直都无法进一步,父亲您甘心吗?女儿知父亲信重吴大相公,可这么多年,吴大相公为何不帮父亲一把,是吴大相公无能,还是不愿呢?”
“休得胡言,朝中之事,岂是你一个妇道人家可妄议的!”阮权被戳中了痛脚,不悦地斥责,却有些色厉内荏的意味儿。
威北侯夫人微微一笑:“父亲,女儿没有妄议朝政,女儿只是为父亲不值。您为吴大相公做了那么多事,得罪了不少人,吴大相公却不愿成全您的心愿,他明明有能力办到的。”
阮权想说些什么,然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出声。
威北侯夫人见状,再接再厉道:“您两日前与我那公爹一道吃酒,公爹如今已是远离朝堂多年,说的话也少有人听,我夫君又远在戎州。父亲,您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阮权沉默了片刻,道:“你姚世伯,爵位被夺,人虽然召回了京城,铨曹却一直压着他帖子,他自己都自身难保。”
威北侯夫人说:“可姚世伯与皇后娘家是姻亲呀。”
阮权冷笑:“就是妖后把你姚世伯夺爵贬谪的,也是妖后把你姚世伯召回京一直叫铨曹压着,他那姻亲有个鬼的用处。”
“可是父亲,您有没有想过,您不愿看到皇后掌权,那王氏也是人人都想皇后掌权的吗?”
阮权看着女儿:“……这怎么说?”
“据女儿所知,王氏大房与二房不睦,皇后对自己嫡亲的二叔多方打压,那王格早就对皇后不满了。”威北侯夫人说:“那姚世伯的正经亲家就是王氏二房的王格,与皇后那边还拐了道弯呢。”
阮权道:“你既说了,妖后连自己的二叔都打压,你那姚世伯还能有什么办法……助我。”
“自然是王氏的事,让王氏的人解决呀。”威北侯夫人笑着说。
阮权看了女儿一眼,心中已经有了计较,遂道:“你公爹是好酒之人,为父正巧得了两坛好酒,你明日回去,转告你公爹,叫他叫上好友一道品酒。”
威北侯夫人脸上的笑有点儿挂不住了,娘家这是铁了心要将她婆家扯进来,她公爹又不想掺和进这些事当中,否则怎会祸水东引,把前南雄侯姚巨川给推出来。
她父亲这样说,叫她回去怎么跟公爹交代!
阮家父女各怀心思,从头到尾没有说话的阮夫人早就听明白二人打的什么机锋,可她到底什么都没有说。
自家老爷谋划权力,出嫁的女儿向着婆家,她还有什么好说的,她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听。
威北侯夫人回到婆家后,把阮权的话跟老威北侯傅绅一说,傅绅登时气笑了。
“行了,我知道了,你自去休息吧。”阮权是个滑头,傅绅没达到目的,却也不能怪儿媳办事不力。
威北侯夫人离开后,傅绅重新铺纸作画,笔悬停在纸上许久迟迟落不下去,他无奈地将笔搁下,将墨滴浸染的纸团成团扔掉。
“唉……”傅绅扶额靠在椅背上,头疼。
他不想家中卷入朝廷的争权夺利当中,他们威北侯府有几斤几两他自己知道,所以才叫儿子自请去南边多山林瘴气的戎州,却还是被各路人马盯上了。
他儿子手里不过区区三万厢军,算上吃空饷的,恐怕才两万出头,还是在那么远的戎州,若京城真出了什么事儿,从戎州过来,哪怕急行军也要半月以上,等他儿子带兵赶到,怕是黄花菜早就凉了。
就这点儿东西都被盯上,这些人真是……
傅绅思来想去别无他法,最后只能心一横,写了一道请安表送进宫中,以期王皇后看到后能召他入宫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