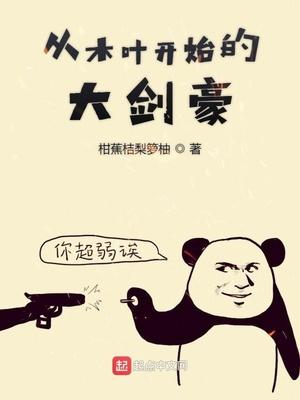墨澜小说>槐火燎原 > 难缠(第1页)
难缠(第1页)
嗓音低沉如闷雷,骤然而响,倒把装作淡然的“崔清婉”吓得一激灵。
这般气势,不必回头她也清楚,是裴如信。
说来差点忘记,作为承乐公主夫婿的胞弟,又是裴家后辈中唯一的成年男子,他早早被授予忠武将军一衔,出现在这种席面上是理所应当。
只是这人向来寡言、更有不动如山的气魄,自入席便一直稳坐后方,默然之下,差点就让人忘记他的存在。
“早就听闻崔、裴两家交谊匪浅,今日一看,果不虚言。”
接话者还是杨家娘子,此时她摇着团扇起身,双颊浅绯,眉眼舒展,颇有几分荣辱不惊的气量,随着她缓步轻移,鹅黄色披帛掠过团花锦毯悄然拖至“崔清婉”身侧。
“只是盛王殿下府中舞姬虽为绝色,可日后总有缘观赏,倒是郡夫人的惊鸿之姿,若此次错过,怕下次再难得见了。”
“汝是何意?”裴如信抬眼凝看杨氏,声线如浸寒江。
“哎呀!都怪妾身笨口拙舌,裴将军定是误会了妾身意思。”
杨氏以扇掩口故作无辜,转瞬又眉眼弯弯,忽地倾身间,她涂着蔻丹的指尖已攀上“崔清婉”肩头。
“妾身不过想着,郡夫人不仅遇难呈祥,就连这旧情也能死灰复燃,当真是京中独一份儿的好福气。”
感受到肩上指尖暗暗发力,“崔清婉”被带着朝杨氏身前近了近,对方丹唇开合间,那染着苏合香粉的热气儿直往她耳廓里钻:
“听闻桓王亲卫在崔府门前守了半月有余,实在是威风得紧——坊巷间,黄口小儿们都竞相拍手嬉闹,唱什么‘断钗合、破镜圆’,如此盛况,比您二位成婚时还要热闹三分,想来郡夫人终于天遂人愿,该续前缘了?”
你有病吧!
气血“噌”地一下上涌,她拧着脖颈对挑衅者怒目而视,那句不合身份的回怼在她喉间冲撞了几遭,最终还是被紧咬的牙关挡了回去。
任旁人是污蔑还是讥讽,她都可镇定自若,但唯独在牵扯到李澈时她忍不了半分。
什么“天遂人愿”?难道是她上赶着要回那个吃人不见血的王府?那算什么好去处?!
“杨女史心直口快,说得这般玩笑话,昔日伤,附体疮,饶是五弟旧情难忘,也得郡夫人原谅首肯才是,岂是你一人敢断言?”
环佩作响,看将过去,原是楚王自渠边坐席上起身,他风姿卓然、气宇轩昂,本与裴如信相仿的年岁,却因少与军营操练而多了份京中贵族独有的雅韵华美。
话至一半,却见李泓斜踱半步走到螺钿榻旁,不知出于何种心态,他探出手轻抚醉酒歇息者睡颜,如此情形,倒像是寻常人家的兄弟情深。
“浓绿余红,郡夫人暮春出游本是雅致,无端被郊外贱民惊扰。而我这五弟虽素性疏阔,然最是念旧重情。得知此事后,五弟深悔当日处置欠妥,一纸书信竟让天下人误以为崔氏女能任人欺侮,故特遣府兵随护,以正视听。”
方才的怒气尚未消散,“崔清婉”又被李泓几句话气得太阳穴直“突突”,她乜斜明目盯看对方,眸中冰冷不加掩饰。
一纸书信?以正视听?
皇室子弟果真满腹经纶,不过绣口一吐,便是整部《春秋》。
早先只觉桓王茶香浓烈,现今一看,楚王才是不遑多让。
“这可奇了,桓王不抓着机会剖白心迹,居然让楚王殿下帮了腔?”
半倾在她身侧的杨氏维持着姿势,对着楚王开口打趣。
乍一看,她二人相互依偎着,竟似闺中密友般热络。
“哎,我只是万般可惜……”
才刚回过楚王,可杨氏并未收声,随着她唇角笑纹堆得愈发浓深,那搭在“崔清婉”肩头的玉手也作势轻拍起来,而故作亲昵的尾音更是打着旋儿地硬挤到后者的耳畔。
“桓王居然如此不解风情,连这般台阶都接不稳当,我们郡夫人可要受委屈咯~”
委屈NM!
……对不起!
下意识骂出脏话,也下意识地道歉,“崔清婉”眉头一皱,抖肩摆脱那只不知分寸的柔夷。
“杨女史为人风趣,说的多是些我听不懂的话,尤其这‘委屈’一词,简直来得蹊跷。”
“众人皆知,桓王殿下与我一别两宽,不知杨女史何时研习了神鬼之术,竟占卜出‘该续前缘’一事?”
纤指拈起丝帕,她拭了拭鼻尖上的细密汗珠,宴席上本就闷热,这接二连三的挑衅更让她心烦。
眼见着杨氏不依不饶地靠近,欲要开口挤兑,她忙是斜侧身子避开,心中愠恼也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我虽不才,却也知晓‘良驹不吃回头草’之理,生而为人,岂能逊于马畜?倒是女史再三提及,莫非真有此癖好,需借我来声张?若‘委屈’由此而来,那我也就为女史受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