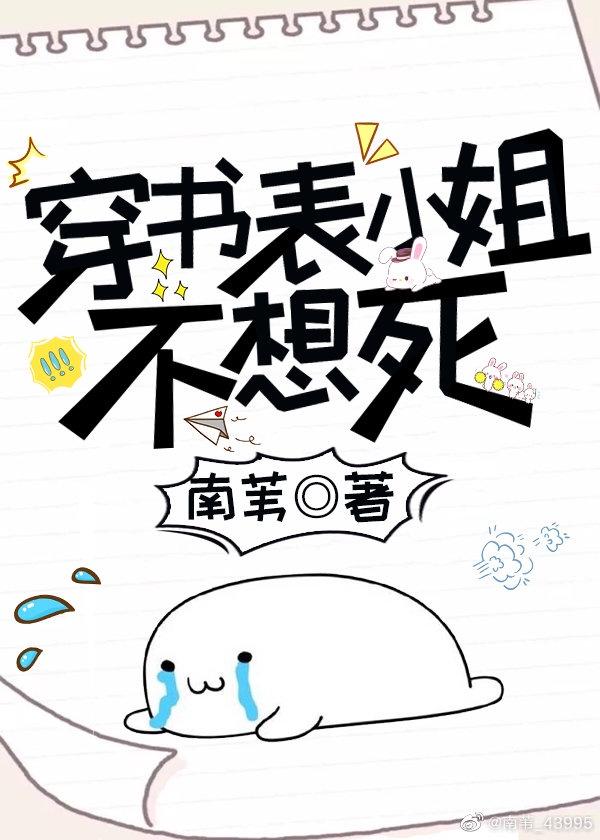墨澜小说>嫁给掌印后 > 第111章(第1页)
第111章(第1页)
“你说的对,母妃怎么可能会跟先太子有所牵扯,一定因为有人长得与母妃相像。”这样的说法,若是细究,简直是漏洞百出,但芷兮宁肯相信这漏洞百出的解释。直觉告诉她,若是去深思楚恬那句话背后的意义,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她所乐见的。她的手指在身侧紧紧握着,脸色还是有些白,想来刚刚受的惊吓不小,冯奕便道:“公主先回去休息会儿吧,也好让红缨替公主看看,有没有伤到哪里。”芷兮心里还是有些慌乱,闻言便顺势点了点头,离开了后院。冯奕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算着她差不多已经回了前院的房间,这才转身,往关押楚恬的柴房而去。楚恬手脚已被绑住,他人也安静下来,复又成了那个不发一语只会傻笑的痴傻之人。冯奕在他跟前站了许久,他都不曾抬头看他一眼。冯奕向四名暗卫使了个眼色,他们便退了出去。“你是装疯的是吗?”过了许久,他才不疾不徐的开口,他虽问,可语气里却是肯定。楚恬装疯,他从一开始就怀疑过,但因为他并不着急从他口中得知玉玺的下落,便也犯不着动刑去审问一个有可能疯傻之人,他只是耐心的替他找了郎中,好吃好喝的将他养在东厂的大牢内。冯奕的话,楚恬并不承认,却也不出声否认,只是如之前那般,目光呆滞的坐着。冯奕倒也不恼,他将自己的披风解下,在楚恬面前蹲下,盯着他的眼睛看了许久,末了淡淡一笑,继而又从自己筒靴里掏出一把匕首。匕首闪着森寒的光芒,楚恬依旧视若无睹。冯奕有些佩服他的镇定,旁人一听到东厂的名号,就怕到恨不能将祖上三代的床帏之事给抖落出来,但楚恬在东厂大牢内待了两个多月,虽没有受刑,但他却日日都能听见其他犯人受刑的惨叫,如此,他依然没有半分惧意。“你听说过‘弹琵琶’吗?”冯奕用匕首在他胸前滑过,又指了指楚恬的胸腔骨,用着最温和的声音说着让人遍体生寒的话语:“用匕首在这一划,再将这里的皮肉往下一撕,就能看见你的肋骨了。”“再找一个铁刷子,在你的肋骨上慢慢的刷来刷去,此刑便谓之弹琵琶。”“不过我倒是不会用在你身上,这么美的名字,用,也应该用在美人身上,你说是不是?”他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楚恬的双眼,果然在那里头看见了转瞬而逝的恐惧。冯奕起身背过他去,缓缓道:“你在禹州装疯卖傻多年,日常吃食几乎都是由乞丐巷巷尾的赵寡妇帮衬。赵寡妇命不好,年轻时嫁了一个只会在酒场赌场混日子的男人,也挨了那男人不少打。后来有一次,她的男人喝多了酒,回家后就对赵寡妇拳打脚踢,赵寡妇恨极,奋起反抗,却不想失手将那男人给捅死了。”“不过乞丐巷的人,都知道那男人平日是个什么德行,他死了,巷子里的人都觉得赵寡妇算是熬出头了,于是大家也就一致决定,帮赵寡妇隐瞒杀人的事实。”“你说他们要是知道,当年那男人是因为撞见你与赵寡妇偷情,才被你和赵寡妇联合反杀的话,赵寡妇还能安然无恙的在乞丐巷生活下去吗?”他颇费了一番功夫,才知道赵寡妇这个人,又从她口中得知了当年事情的真相,从那之后楚恬就疯了。冯奕猜想他装疯多半是为了不让人怀疑自己与赵寡妇的关系,毕竟没有人会怀疑貌美的赵寡妇会看上一个疯子。说完这番话,冯奕便噤了声,屋内依旧安静,但却多了一道粗重的呼吸声。他无声的笑一笑,便即转身,楚恬终于对自己所说的话有了反应,他正用着与方才面对公主时同样的眼神瞪着他。“我与她,不是偷情。”楚恬终于再次开口了,他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她的丈夫动辄对她打骂不休,我看她伤心,不过是去安慰她罢了。”谁知那男人好巧不巧的提前回来了,他不听任何解释,一味认定他们在偷情,拿着菜刀不管不顾的朝他们砍过来,楚恬不能等死,只能奋起反抗,随后意外就发生了。“你们是不是偷情不重要,人是不是你们一起杀的也不重要。”冯奕停顿了片刻,继续道:“重要的是,你之所以会留在禹州,是因为赵寡妇。”“你想对她做什么?”楚恬额上青筋暴起,脸上的皱纹每一条都诉说着他的愤怒。冯奕依旧云淡风轻,“我对她做什么,取决于你做会什么。”楚恬低下头去,眉头死死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