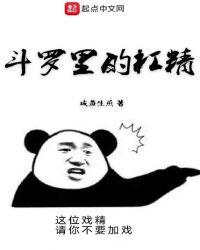墨澜小说>殿下好风流! > 第143章(第1页)
第143章(第1页)
就皇子所配之物来说,这金葫芦实在算不得贵重,一眼便看得出是宫外民间之物——文妃母家世代清流,自然没有财力送贵重稀罕物件,但民间都有葫芦辟邪一说,这小葫芦又是他贴身佩戴,显然他极为珍视。
萧彦便认真接过,把绳线结实绕在手腕,给他瞧:“多谢,有你这个宝贝,二哥定能驱散鬼魅、逢凶化吉。”
萧意宽慰地点头,忽又想起自己没了葫芦护身,还要穿过前方偌大皇陵,脸上不免又露惶恐:方才混乱之时,似乎没人顾及自己。从前他视君父为靠山,但最近数次经历让他已然发觉:即便紧跟在君父身边,也不觉得安全。
萧彦知他所想,拍拍他肩膀:“咱们大魏萧氏男儿,自当勇往直前——此地有先祖庇佑,没人能伤你。”
萧意攥攥小拳头,鼓起勇气追着众人去了。
门外光线照着殿内俊美冷静的脸,渐渐变为光束,随后消失。
——门前并无人影,但两扇殿门已悄悄地合拢。
刺客都已变成了尸体,堆在屏风后。
萧彦从容站起,孑然一身立在后殿中央,重新握匕首在手,屏心静气,准备迎敌——虽然他之前预判了萧章的所有动向,却不曾预料到,最后君父会留他在此处。
方才去前殿传召他的内监从柱后无声走出来,早无伪装的怯懦,一脸惋惜地看他。萧彦这才注意到,这内监身形明显较方才高大一整圈,原本宽大的衣衫显得短小紧促。
他仅仅怔了片刻,笑着猜道:“——大监原来也是个‘托达’?倒没看出你却是犬戎出身。”
内监也笑:“恭王殿下博闻广知,但这缩骨之术却并非犬戎独有,只是数百年来几乎无人知晓的暗卫秘术罢了。”
萧彦点头:“原来如此。本王之前还曾纳罕:按说宫中防卫最该警惕,可本王向君父禀奏过‘托达’一事后,却不见宫中有什么预防之策——原来本就无需加强防卫,君父身边便是和‘托达’一样的人。”
内监愈发惋惜:“亲王之中,您乃是一等一的聪慧。”
见萧彦仍对着门外,不免提醒道:“恭王殿下,您那两个侍卫自身难保,不会来援了;眼下您该专心解困,怎么还盯着门外盼呢。”
另有一人从对角走出,对他行礼——两人都空着手。
处决皇族,历来不能施加兵刃、破坏身体。
萧彦笑着摇头:“君父并无明旨,本王才不会束手就擒。”
那内监叹道:“您明鉴,您何等尊贵?若非圣上旨意,咱们怎会如此?”
萧彦淡淡道:“本王有何罪?今日礼王公然谋大逆,尚且被带回宫发落;本王却连一旨明诏也无,就要在此地、逆贼尸身旁,一起被了结?”
那内监叹道:“究其原委,其实您自个儿的话里不都说明白了么。”
建德帝子嗣并不昌隆:长子早年夭折,如今萧竟病弱,萧章谋逆,萧意年幼;而他萧彦并无大罪,却要被假借刺客一事不明不白地了结。
为何建德帝毫无征兆地突然执意要杀他?虎毒尚不食子,除非——
萧彦猛然醒悟。
之前首阳暗中谣言:恭王生于勾栏,实则血脉存疑,并非真正的萧氏后代。
谣言无稽:建德帝心思缜密谨慎,以他之能,绝无可能在血脉之事上被欺瞒;若是哪怕有一处微小疑点,他萧彦便绝无可能活到现在——因此萧彦从未怀疑过此事。
谣言起后,宫中毫无动静,很快便无人再传——谁敢诬蔑皇帝戴了绿帽、养着非亲生的儿子?!
但谁料却有今日。
萧彦这一惊全无防备,但立即冷静,仍然镇定道:“君父不过一时中了奸人离间之计,且待本王与母妃在御前自证,便清者自清。”
他往门迈出一步,那内监便随之靠近一步,耐心劝道:“您是聪明人,若是圣上容您辩解,又怎会留您在此?您平定南北,也出生入死,咱家敬服您功业;不若您且阖眼,咱家动作很快,您便能去的安详。”
这两人数年来都是唯唯诺诺、端茶送水的内监身份,此时空手对他,却十分放松——看来君父为保绝密、不在事后让人查出任何动用人手的迹象,不惜隐藏启用身边隐藏最深、实力最强的暗卫。
萧彦不答,匕首虚晃一道银影,人往殿门掠去——对方是御前高手,以一对二,他自是敌不过,可他也绝不引颈就戮!
两个内监紧紧跟上,截住他路,仍然劝道:“您出去又能怎样?这会圣上想必已把所有人带走了,不会有人看见——即便有人看见,同样也得留下。”
萧彦稳稳挥刀如电,不为所动:“今日本王王妃册封,本王自要去见他。”
那两人与他交手之间,神色渐渐认真起来:“恭王殿下身手超出咱家预料。但您若执意抵抗,恐怕保不得您仪容安详,待会王妃见了难免悲伤。”
两个高手联合,萧彦尽管拼尽全力,终是难敌,被封住去路,半步也前进不得。一个不慎,手中匕首被夺,扔在门边。随即一掌拍下,萧彦无法,只好硬生生抬手格挡——
一声闷响,本以为手腕折断,却是萧意留给他的小葫芦碎成了两半。
但这力道萧彦却仍招架不住,身不由己滚倒在屏风前。
不等他爬起,内监的冰凉大掌继而直冲他脖颈而来。
生死边缘,萧彦眼前闪现的唯有谢承泽的脸:不知他现在何处,有没有被带出皇陵等待自己;即便过后赶来,这殿中留给他的却只有自己冰凉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