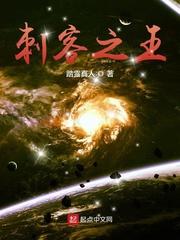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嫐(沟头堡的风花雪月) > 第4章 风云(第7页)
第4章 风云(第7页)
为了防止继续长大个儿,双保险之下焕章扔给杨哥一根烟,又摇身一变成了讲解员,不过他不姓韩,姓赵。
书香歪起脑袋打着了火,很快就从桌子底下找到了所谓的烟灰缸——午餐肉报销后的空盒子——黑糊燎烂,里面堆了半罐烟屁。
呜咽的风一直在刮,呼呼的,而鼓掌声由远及近,半是停顿半是铿锵,在隐约听到一声“屁屁”之后,紧接着就是一道更为响亮的鼓掌声,随之而来的还有女人沙哑的呻吟,好像被什么撕裂了一般,在躲闪中偶尔迸发出来,很快又归于沉寂。
撞击声越来越大,而且看起来更为持久,齉鼻儿的喘息也变得焦虑起来,以至于声音走形,如同一口痰卡在喉咙上,将死之人在拼命倒着最后一口气。
这一通捣鼓,女人终于泄出气来,甚至还可以感受出声音的颤抖和紧绷。
“咋还要?”
她说,“都几次了?”
假音儿在音乐的伴奏下有些急赤,唯恐避之不及却无巧不巧地撞上了,又发出了一连串夹带起空灵的声音,“还让,不让人活?”
齉鼻儿不为所动,吧唧起嘴来,尽管一时像极了婴儿,却总让人觉得他特没出息,尤其最后,就跟没牙老吃柿子似的,吸溜吸溜的,女人就在短促的呻吟后开始拉长了音儿。
“屁屁”吃过柿子,齉鼻儿这鸡巴嘴叨咕个没完没了——发出来的也是假声。
“咋样?”
他问。
女人只是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睡睡”,在喘息中变得沉寂下来,被歌声掩饰。
约摸有个小半分钟,嗒地一声传来,女人问了句:“几点了都?”
明明是在质问,听起来却绵软无力。
“不才三点吗,离天亮还早着呢。”
齉鼻儿嘻嘻哈哈,假声透着喘息,鸡巴嘴跟鲶鱼一个揍性,“穿上。”
又过了会儿,他拱起猪鼻子来,哼哼不断,随之而来的是有节奏的啪叽声。
女人的哼吟又开始了,时断时续,分明就是在躲闪,但在齉鼻儿的夹击下很快她就失去了抵抗。
“屁屁。”
这称呼太他妈个性了,但女人不反对他就持续这么叫,“给你来点东西。”
女人哼了一声过后竟然没去追问,可能是不屑,也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呜咽声分明大了些许,音乐也跟着摇晃起来,于是雨打芭蕉汇集在一处,在掌声雷动下变得乱糟糟的。
“啊不行,啊来啦。”
突兀的声音在沉寂片刻骤然从女人嘴里迸发出来,打破了平衡,瞬间又变成了倏急的喘息。
“爽不爽?啊,爽不爽?”
齉鼻儿连续粗吼。
女人间歇性喘息的同时,猛地来了个高音儿:“爽。”
不过,在岁月之声的泉溪流淌下,听起来都有些沙哑变形。
“什鸡巴玩意?”
录就录还鸡巴插播音乐,“妈个屄。”
焕章脸一红,发觉杨哥也好不到哪,就又扔给他一根烟,不知不觉,哥俩这已经抽了两三根。
“你听,这女的高潮了。”骂归骂,可听起来还是很有感觉的,他就在嘿嘿嘿中用卡巴裆表示出个人看法。
似锦繁华的城市好在哪,而低矮的村落又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待见呢?
夜幕闪耀,村边流淌的小河,树影绰绰婆娑,返城和迎送,在知青的一句“谢谢你给我的爱”中,美丽的大辫子姑娘眼睛里淌出泪花。
这是李清波的歌,却被齉鼻儿哼唧出来。
女人一个劲儿地“啊啊”,如同空谷回音,本是有前劲没后劲,却硬生生给榨出来了:“给我啥?”
涓涓细流一下子就跨越了年代,的确良、千层底,再久远便是把头耷拉下来,受气包似的——我承认我有罪。
“精华。”
这场持续近四十分钟的战斗在这声精华下似乎要宣告结束了,于是齉鼻儿大吼起来,但仍旧是齉鼻儿,嘎嘎地,比房书安还房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