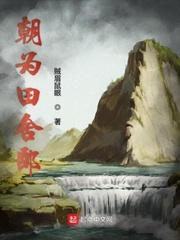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我和我的母亲(寄印传奇) > 第62章(第2页)
第62章(第2页)
我想说点什么,结果只是在擦肩而过时“嗯”了一声。
酒劲儿似乎下去了,但那种眩晕感却奇怪地保留下来。
我不由单手操兜,挠了挠头,然后——回头瞄了一眼。
不料,母亲压根站着没动。
她双臂抱胸,说:“还玩呢。”
只觉面门一热,我又是下意识地一声“嗯”,与此同时拧开了书房门。
“早点儿睡,也不看看几点了,啥坏习惯一天。”等我关上门,客厅才响起脚步声,母亲又补充一句:“嗯嗯嗯,嗯个屁嗯。”
母亲应该去了趟卫生间,有个四五分钟才回了房。
我不知道父亲能否如愿,但说不上为什么,心里总有些烦躁莫名。
雪非但不见小,反而猛了几分,在茫茫黑夜中铺天盖地,瞅着怪吓人的。
等周遭安静下来,我才回到电脑前,戴上了耳机。
想了想,又起身熄了灯。
荧光刺目,我抿了口冷牛奶,打开了第六个视频。
黑咕隆咚中渗着一抹淡蓝色的微光,或许是成像问题,氤氲得如一团薄雾。
一条黑线自上而下把薄雾一分为二,接近底部时又隐隐开了个八字形的小岔。
“捺”的右侧立着半张屎黄色的桌子(也可能是棕褐色),近乎占去十分之一的画面。
桌子往上是一张单人床,朦胧的白色覆盖着一具柔软的胴体,青丝散在枕间,再融入那片黑咕隆咚。
光源当然来自窗外,甭管原先是什么颜色,透过一袭蓝色窗帘后难免就沾染上了蓝色,这种事毫无办法。
背景音有点大,说不好是杂音还是什么在摩擦,倒是鼾声和偶尔的汽车鸣笛清晰可辨。
显然此视频之前看过,我还真是反应迟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画面几无变化,起码肉眼难以捕捉。
女人在酣睡,我试图看清那张微侧着的脸,却徒劳无功。
如此煎熬了七八分钟,再也挨不下去,只好揉揉眼,拖起了进度条。
反复拖拽和快进了了几次,直到视频的第三十一分钟,耳机里才传来了异常响动。
窸窸窣窣,吱吱嘎嘎,“老牛!”
近乎耳语。
又是一阵窸窸窣窣后,周遭安静下来。
有个十几秒,“老牛!”
这次声源稍微远了些。
很快,一抹白色鬼魅般打画面的左下角闪现,快速飘至单人床前。
这货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真真吓人一跳。
紧跟着,他背对镜头俯下身去,靠近了床上的女人。
于是淡蓝色的薄雾轻轻抚起白衬衣,露出一对枯瘦的光屁股。
我甚至觉得可以在那抹黑暗中辨认出他的蛋。
这难免又吓人一跳。
陈建军——如果真的是陈建军的话,左手抚上那袭朦胧的白色,右手按在床头,嘴里念咒般一阵嘀嘀咕咕,随后整个人缓缓蹲下,那颗猪脑袋几乎要消失在青丝间。
清晰的吸气声打暗淡的画面中升起,猥琐、诡异而又夸张。
邪教仪式以女人的弹起宣告结束,她一声轻呼,随即被男人捂住了嘴。
白衬衣在笑,嘿嘿嘿的。
女人挪了挪身子,似乎说了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