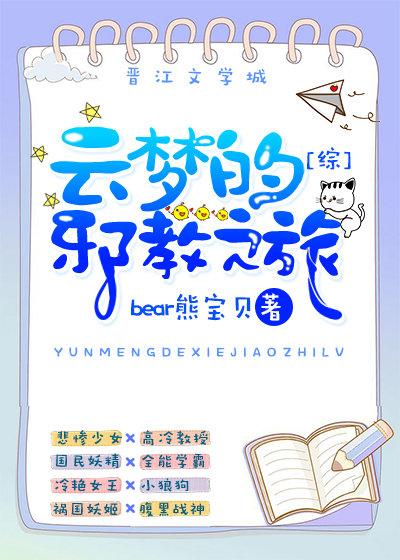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谋娶臣妻 > 第246章(第1页)
第246章(第1页)
薛岑有听没懂,拨弄着她脚踝旁边的小铃铛,有点爱不释手。作者有话要说:鲜笋琴濯觉得自己说的话在薛岑耳朵听来大约都是反义,越说“不”这人就越上头,可她到底也不敢真的顺着他了,因为知道等着她的一定是个大坑。她被脚腕上的手触得发痒,忍不住蹬了几下,清脆的铃铛响起来十分悦耳。房门还大敞着,外面的春色亦倾泻而入。卧雪正在阶下扫着落下来的桃花瓣,她跟着琴濯有些时日,了解她平日的习惯,听她说回头要用这些落花晒干了制些香包,一得了空便过来收拾了。她听到那摇得清脆的铃声,由不得抬了下眼,看到房里遮在广袖下的一对并拢的玉足,正羞赧不安地在白底云纹的衣料上蹭动,当下心里一绷,地上的花儿也顾不得了,垂下眼便退了出去。房门随后被合了个严实,只有窗缝之间连续不绝传出来的清脆铃声,叮叮当当地随着春风摇曳半晌。枝头春红也到了尽头,飞鸟掠过的动静都惊落下来缤纷一片,转瞬便将干净的台阶又粉莹莹覆了一层。卧雪从别处收集了一些,过来后院见那厚厚的一层,任由其沤坏了也是可惜,便将上面没有沾到浮土的一层揽了些,装在绢袋里一并拿给琴濯。早些时候薛岑还在,卧雪只来送了水,没有吩咐也不敢在此多逗留,等到快用晚膳的时候方才过来。琴濯照旧歪在那张软塌上,半耷着眼看起来春睡未醒的样子,与旁边插花的瓷瓶上云鬓低垂的美人神态一致。“好丫头,我倒忘了说,难为你记得!”琴濯看到卧雪手里的绢袋,睁起眼皮朝她招了招手。卧雪走过去,把口子摊开一些放在榻上,顺手将琴濯身后的软枕往高垫了垫,好让她靠得舒服一些。琴濯捧起一掬桃花瓣闻了闻,有些昏沉的头脑瞬时被花香所浸染,略微清明了些。“还是这个香味最正,晚上拿一些来泡澡,剩下的都晒起来吧,用纱布盖上一层,免得掺入太多浮土。”琴濯说罢,抓了一把花瓣洒在塌边,一侧身就能闻到清淡的香气。卧雪点点头,收起袋子起身,脚底踩着一个东西,低头一瞧捡了起来,“这银质的铃铛果真有些不耐,已经掉下来了。”说着目光落向琴濯的脚。琴濯看到那掉下来的一颗小铃铛,像是忽然想到什么,翻身而起,扒拉起裙边将那铃铛手串全部解了下来,丢到了一边。“吵得人头疼!”卧雪有些不明白,她先前还说这铃铛声好听,怎么这会儿就不喜欢了,不过她脸上气鼓鼓的,说是不高兴倒也并非,想来又是在跟皇上赌气,心下了然不再多言,将手串跟散碎的铃铛收到了一起。薛岑那厢忙完,就跑回来跟琴濯用晚膳了,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看到她悬着脚坐在榻上,走过去便问:“那铃铛怎么不戴着了?”琴濯冲着他膝盖就是一脚,红润的脸都狰狞起来。这个色胚子!当她傻呢!薛岑握住她的脚踝,倒是跟上面一个浅浅的拇指印儿吻合上了,更是完完整整证明了他的“罪证”。看了眼桌上摊着的铃铛,薛岑伸手捞了一下,叮叮当当又掉下来两个,便又丢了回去,“赶明儿给你打个新的。”“我才不要戴,要戴你自己戴!”琴濯觉得自己现在脑子似乎还存着叮叮当当的回响,这人混起来就没完……薛岑的嘴角始终扬着,也没计较她那些明显语气存着怨的话,侧身坐在一旁,拢过她的脚给她套上罗袜,“虽是春日,夜里也冷丝丝的,别太贪凉只穿那凉鞋子到处跑。”琴濯哪里还敢穿,心里想着回头定把那鞋子跟铃铛一并扔了。薛岑仔仔细细地把鞋子给她穿好,方才抱着她的腰将她放到地上,并未松手,当先问她:“还能不能走得动?带你出去逛逛。”琴濯听着前半句又欲掐他一记,听到后面的转而缓和了神色,脚下也站得稳了些,“去哪里?”“昨天不是念叨着想吃春笋?今天带你去吃个够本。”说到春笋,琴濯觉得自己齿间已经忍不住泛起那嫩嫩的口感,当即腿也不软了,腰也不疼了,迫切不已地拉着薛岑往外走,“那快些,再晚了吃一肚子又要压床板。”薛岑看着她矫健的步伐,微微抬了下眉,觉得自己还是低估她了。钱州的春天总比京城来得早一些,春笋是这个时节最为人所乐道的东西,大街小巷的饭馆里都是应季菜。薛岑带着琴濯来到一家专门供春笋的店,这里都是由客人们自己选好笋子,然后才交给厨房,任意煎炒油炸,一应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