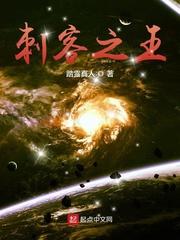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暗夜水火[民国探案] > 第151章(第1页)
第151章(第1页)
“炎曜呢?”水影虚弱地问。
李皖眼眸闪过一丝阴鬱,隻是道:“你放心,他在另外的营帐。”
“我想见他。”水影说。
李皖却没有回答,隻是坐在那裡,目光複杂地盯著她。
“你不让我见他?”水影自嘲地一笑,“也是,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怎么能吩咐堂堂少帅做事?”
“影儿,你别这么说。”
李皖匆忙地抬起手,想要解释,水影却不自觉地往后。
也许是被她防备的目光刺痛,李皖难以置信地说:“你……怕我?”
“你不要伤害他,有什么事冲我来。”
水影明亮的眼眸让李皖有些受伤,“在你心裡,我就是这样的小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踩你的士兵,我已经派人废瞭他的手。”
“你怎么还是不懂,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情瞭,也请你不要为我伤害其他人……”
没等她说完,李皖道:“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可是上天却偏偏跟我开玩笑,让我伤得你这么深,如果你能解气,我愿意当著所有人的面让你还回来那几鞭子,大丈夫一言九鼎,我说到做到。”
“小李,我不会打你,也不会报複你。”
听到水影重新叫他“小李”,李皖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可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难以接受。
水影说:“隻要你放瞭我和炎曜,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咱们还是朋友,和以前一样。”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想和你当的,从来就不是朋友,我想你做我的……我的……”李皖深吸一口气,抓住水影的手,说:“我想你做我的妻子,唯一的妻子。”
水影抽出瞭自己的手,“可是我已经心有所属瞭,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祝福?可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诅咒,我小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幸运的人,所以要什么,就隻能自己去争取,无论是喜欢的人,还是喜欢的东西,都是一样。”
“可无论怎样,也不能残害生命,这是做人的底线。我今天之所以不在穗儿的帐篷,就是因为案子有蹊跷,马奔就像是棋盘上的棋子,下棋的另有其人。”
李皖的眼神似乎有些回避,“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你知道么?我去询问瞭他的同班,有人看见,他曾经单独见过少帅,您和您的父亲,就是下棋的人吧。”
水影话语中的疏离让李皖震惊,可她没有回避,而是继续说:“一开始对于杀人动机,我都隻是拘泥于小情小爱,却没想到,这会不会是一场权力的阴谋?您的父亲李督军对卢少霖明面上器重,实则忌惮,如果放任他做大,会损害他儿子,也就是您的地位。所以他制造瞭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除掉卢曲二人,为瞭加一重保险,便派少帅过来,不让计划发生变故。”
“你是什么时候猜到的?”李皖的脸色很不好看。
“在马奔自尽前,曾问瞭少帅关于他傢人是否会被牵连,而少帅却能清楚地说出他有母亲和妹妹,当时我就觉得奇怪,马奔隻是万千小兵中的一个,少帅是怎么知道他傢人的情况的,后来却想通瞭,棋手自然是瞭解手中棋子的,否则怎能将棋子的效用发挥到最大呢。”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迟迟不与我相认的?宁愿挨瞭鞭子,也不愿意告诉我你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人。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李皖的目光中带著疯狂,还有决绝,让水影感到陌生。
水影说:“我隻是不想事情变得麻烦,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隻想悄悄地离开,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这个世界充满瞭算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却没有什么能够制衡大鱼,他们为所欲为,草菅人命,可是现有的法律,隻能针对普通的虾米,即使大鱼杀瞭人,却不会被怪罪,可悲的是,我也隻是一个虾米罢瞭,什么也改变不瞭,即使找到瞭证据,大鱼的地位也不会被撼动。”
“你知道不知道,我也很痛苦?”李皖抓住水影的肩膀,强迫她看著自己,“父帅说,卢少霖现在越来越不听话瞭,曲光明就是他的智囊,如果放任二人不管,很可能就自成一方势力瞭,到时候鞭长莫及,还不如趁现在,杀掉他们,以绝后患。如果就明晃晃地杀掉他们,很可能会让军营哗变,说我们亏待有功之臣,所以就让马奔假借阴天子的名义,除掉他们。可是,我不想害人,我真的不想……”
水影难受地闭上眼睛,“我不想卷入这滩浑水裡面,炎曜也不想,放我们走吧,这种残忍的权力游戏,一点也不适合我们。”
“为什么你到现在心裡想的还是炎曜?我到底哪裡比不上他?”
“小李,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原本就不需要比较啊,就像两块石头,谁也不能说哪块好,哪块不好吧。”
“可是石头没有傢,它的位置经常是偶然的。”李皖心想,如果我今天放手瞭,也许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瞭。
二人没有再说话,谁也说服不瞭谁,也许世间之事本就是一团乱麻。
剪不断,理还乱。
三天后。
这天夜裡,水影睡得很浅,半夜时分,突然听到人在耳边叫她,“影影,快醒醒。”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水影睁开眼睛,居然是炎曜。
原来他迷晕瞭守卫,换上瞭皖军士兵的衣服,偷偷过来,想将水影带走。
“他没有为难你吧。”水影目光凝重,生怕李皖对炎曜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