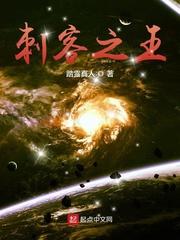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不臣之心 > 分卷阅读184(第1页)
分卷阅读184(第1页)
源,正瞧见一名儒生眼神直愣愣地看向他们这边,连手里的墨块掉在地上都不觉。还是那人旁边的儒生在旁推了推他,那人才反应过来失礼,有些紧张地站了起来,手脚慌乱不知道该不该过来,末了只是拱手朝裴玉戈这边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歉意。裴玉戈出声道:“公子自便,在下与友人只是忽闻异响,并无责怪之意。”那人直起身,目光落在裴玉戈脸上,脸颊涨红,慌忙闭上眼又沉默一拜,躬身呆站着好一会儿,直到一旁的友人拉了一把,他才尴尬地起身坐到了原本对面的位置,这回是背对着裴玉戈了。叶虞倒是能理解那读书人,若非他与裴玉戈从小一块长大,早已看惯了那张雌雄莫辨的脸,只怕方才也会看痴了去。“你说的…我回去后告诉父亲。”叶虞开口,算是为裴玉戈刚刚的那番话表了个态,继而又问道,“你今日回家去,除了习武,是不是还为了东江新王的事与裴伯伯商量?”裴玉戈点头。“父亲虽与裴伯伯是好友,可叶家如今情势,来日怕是帮不上什么忙。”叶虞今日来寻裴玉戈,既是为了一解心中疑虑,也是帮父亲带话。京中得天子倚重的武将就那么几人,叶裴两家交好是京中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天子可以不理会裴绍和叶飞林私交如何,但事关东边将领的人选,叶家确实不适合开口,也是如今叶虞没了千牛卫中郎将的职务,才好以普通友人的身份来说这番话。“无妨,此事我已有把握。重华,你一直说旁人的事,可有为自己将来打算?”“尽管余大夫妙手回春,却也扭转不了毒侵肺腑的事实。月娘如今还不能起身下榻,我……如今不过一介白身,一时也不知道将来能如何了。”叶虞自嘲地笑了笑。他本是前途无量的少年将军,如今骤然被党争牵累,不仅伤了身子还丢了官职,陡然跌入低谷,不免有些沮丧。裴玉戈不管其他,只沉声反问:“你甘心?”叶虞抬头看他,面上虽有犹豫之色,最后还是摇了摇头。“那便养好身子,以待来日。”“嗯,我听你的。”见叶虞面上已有倦色,裴玉戈清楚这是他大病初愈体虚乏力的缘故,便道:“重华,你今日出来的时候久了,我送你回府去。”叶虞是坐裴玉戈的马车到书斋的,先前叶府的马车没有跟来,裴玉戈便提出送人回去,叶虞也是真的有些乏了便没有拒绝。二人起身下楼,只是刚走到一半,便听得一阵喧哗之声,夹杂着他人叫嚷呵斥的声音。裴玉戈下来时,正遇上徐正礼匆忙过来,似乎是正打算上楼去请他,而书斋的掌柜正站在门口同人说着什么。“大公子,有人来闹事,还带来了京兆府的人。”“缘由?”“说是怀疑白掌柜窝藏逃奴,又说许旁人借书有邀买人心之嫌,要封了书斋并拿了人去问话,不过依属下看……似乎不像是为了抢生意来的。”闲余书斋在京中开了好多年,做的也是赔本买卖,根本抢不了那些正经卖书的生意。徐正礼这话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既然不大可能是为了生意,那便只能是冲着人来的,而白掌柜只是个寻常的小生意人,根本没什么值得人惦记的,若说怀疑,徐正礼自然而然会猜到自家公子身上。
裴玉戈扫了眼,心中想的却与徐正礼暗指的不同。“东家!救我!”白掌柜是个平头百姓,架不住那些官差气势汹汹上来抓人。书斋内原本借书看的读书人早被呵斥出去了,有几个楼上的听到动静也下来几步看看是什么事。京兆府的官差原本是奉命拿人,刚刚听到白掌柜求救,自然而然将目光落在了走过来的裴玉戈和叶虞身上。裴玉戈今日去侯府习武,自然穿得是一身利落劲装。他人清瘦高挑,配上那张绝世容颜,登时晃得那些官差眼神痴痴的,一时没有动作。为首的那个眨了眨眼,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而后脸上马上露出意外吃惊的神色,显然他是认出了裴玉戈是谁,但同时又十分意外裴玉戈怎么会跟这间书斋有关联。仅仅是那一瞬最真实的反应也被裴玉戈看在了眼里,再扫一旁管家仆从打扮的那伙人,便证实了他心中的猜测——京兆府的人是为‘某些人’出头挑事,但并非是冲着他来的,所以那名认出他的京兆府官差才会露出意料之外的神情。不过同来的那伙人显然是不识得裴玉戈和叶虞的,管家模样的人抬手便指向裴玉戈,盛气凌人质问道:“你就是这书斋的东家?”裴玉戈未答,只是将目光转向京兆府的人。领头的官差立刻凑上来拱手客气道:“卑职见过裴大人。不知裴大人在此,有所惊扰,万望大人见谅!”同行的那伙人显然没想到京兆府的人态度变得这么快,领头的管家眼珠一转,意识到裴玉戈的地位不低,再一想京中有此倾城容貌还能被叫做男子的大人能是谁,也立刻收敛了刚刚的气势,面上带着假笑道:“见过大人,小的乃是阆中院转运使赵大人府上管家,今日同京兆府的官差来此是因为书斋掌柜前些时日收留窝藏了府上的一名逃奴,又不肯将人交出。我家大人这才遣小的报官,只为带回逃奴,未曾想这里竟是大人的铺子。”赵之文与礼王府有关,裴玉戈近日原本就在整理参奏那两个姓赵的,今日倒是碰巧撞到他跟前,没道理放过。裴玉戈看向白掌柜,只淡淡道:“白掌柜,可有此事?”白掌柜立刻道:“东家,我敢赌咒绝无此事!”“白掌柜是个本分老实的人,这点本官倒是能为他作保。”目光扫过京兆府的人,裴玉戈语气冷冷的,“既已报官拿人,想来人证物证俱全。”赵府的人立刻说:“我们有人证!府里的人亲眼看着那女人躲进书斋再没出来!”裴玉戈闻言忽得笑了一声,也不搭理赵之文府上的人,转而看向京兆府的人,问道:“报官的和人证是一拨人,巩大人何时这么草率了?”话说得不重,可从一名御史的嘴里说出来,那分量便格外重了。领头的官差被盯得汗都下来了,怕说话一个不小心让自家大人明日被参,又怕不回更要命,急得牙关直打颤。偏此时他又听裴玉戈接着质问道:“可还有别的实证?”赵府的人想张口,被那领头的官差一把子按住,陪着笑脸道:“巩大人这两日身子不适,今日没来府衙,是卑职一时考虑不周,偏听偏信搅了裴大人的清净,还请大人恕罪!我这便带人回去重新细细盘问,必不使人受委屈!”那官差应是京兆府尹的心腹,关键时候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左右祸事还没完全酿成,裴玉戈堂堂御史中丞也不会揪着他这个末流的差役不放,而保全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