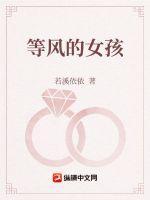墨澜小说>水晶露珠(蓝色酒馆之十)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方良善人如其名善良又不擅记恨,胆子小没什么脾气,三分钟前发恼的事她会在三分钟后忘得一干二净,不会钻牛角尖的自叹不如人,顶多钉钉草人发泄发泄而己。
她的个性像小孩子,一点好事就令她高兴个老半天,不愉快的事嘟嚷两声便无疾而终,是十足没心机的软柿子,让人想去欺负她一下。
不过那种欺负不是真正的伤害,而是取笑或戏弄,让胆小的她气得牙痒痒却不敢发作,只能扁着张嘴叨叨念念。
“什么工作有红包可赚?”似乎来得过份容易。
“西索米。”她说得可得意了呢。
“什……什么?”不会是她想的那一种吧?被口水梗了一下的herit差点被冰凿刺穿掌心。
她记得她学的是服装设计,副修管弦乐器,不太可能会赚这种钱吧!
“你也不要想得太悲苦啦!一个小时就有一万块进帐很不错呀!是我半个多月的薪水耶!”她满心感恩的双手合十一拜。
她是助理兼打杂的兼茶水小妹兼清洁工,反正一间三、四十坪的工作室全由她一人负责,地上多了一张纸屑也归她管,月入一万三千五百元,是所有人中工资最低微的一个。
虽然他们的工作伙伴包括模特儿一共有十来人,可是大家看起来都比她忙,一会修指甲、一会儿打粉底,好像她不做都不行,不然挨骂的准是她,没人会为她说情。
月薪其中五百块是全勤奖,迟到一分钟奖金就没了,所以她几乎全年无休的为生计打拼,少了那不起眼的数字她连基本电话费也缴不起,犹如一级贫户。
并不是说她的开销大或过于浪费不懂得节流,而是她把将近一半的薪水寄回育幼院,曾经是其中一员的她不希望如同母亲的院长太过劳累,在她能力范围内她想尽量回镇抚育她成人的家,即使自己过得很清苦亦无妨。
但她不算是孤儿,自从她无意间与亲生父亲重逢后,她有了一个家,不过此事说来话长颇具戏剧化,不提也罢。
“亏你乐观想得开,像野草一样充满韧性,不管多恶劣的环境都能生长。”像她就不行了,她懒得为生命冲刺,只要环境不适合她立刻放弃,绝不妥协。
“没办法,你也知道我同学钟丽艳家是开葬仪社的,刚好人数不齐找我凑数……”而她又凶又恰又会横眉竖眼,她根本不敢摇头。
“你真好说话。”怕她喝醉的herit特意在她的酒里多调了蜂蜜和番茄汁,酒的份量减少三分之一。
“什么好说话,我今天差点吼了送葬的人,很想把鼓举起来砸在他们头上。”方良善气呼呼的说,两腮涨红像偷抹了胭脂。
“你?”冷酷的眼流露出深沉的笑,herit非常明白她的胆容量有多少。
她很气的一口喝光杯里的酒,豪气的用手臂抹去酒渍。“我告诉你,他们实在太过份了,明明是丧事大家哭得一场胡涂不知今夕是何夕,可是我往他们面前一站,所有人都笑了,好像死的人是他们的仇人而不是亲人。”
太可恶了,她没那么好笑好吗?
“我了解、我了解。”不能笑得太明日张胆,一定要忍住。
“一群披麻带孝的孝男孝女居然用扶灵的手指我的脸耶!他们才刚摸过死人……”想起来就毛骨悚然,不晓得会不会被煞到。
一阵大笑声由她身后飘过,十分同情她际遇的jas送上一朵扎成玫瑰的金莎巧克力,希望她不要太……爆笑。
喔!肚子好痛,不管从正面背面看都觉得她像一只会用两只脚走路的长毛吉娃娃,而且她还用可爱的小手捧着酒杯,那“温馨”的画面让人不由自主的扯动脸颊“会心一笑”。
如果不听她言谈内容或许还稍稍能控制笑意,可是……不行了、不行了,先让他爆炸一下,不然他会把酒洒在客人头上,只因神经抽搐过度。
又、被、笑、了。“herit,你想我需要整容吗?”
看她咬牙切齿又不敢发作的表情,herit的笑声如流水轻泄。“呃,千万不要,天生万物各有他存在的必要,用不着太在意。”
“是具有娱乐效果吧!”方良善小声的低喃着。
“嗯,你说什么?”瞧她嘴巴动了动,八成又在说令人好笑的话。
张口欲言,她瞧见陌生男子在她身旁的位子落坐,身子连忙一避躲到更僻静的角落。“算了、算了,我要走了。”
像是说给自己听,她笨拙的从高脚椅上滑下来,眼睛盯着胸前小小的绿玉坠子,就是没胆子四处张望,安静得像怕人发觉的小老鼠,只差没蹑起足尖贴着墙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