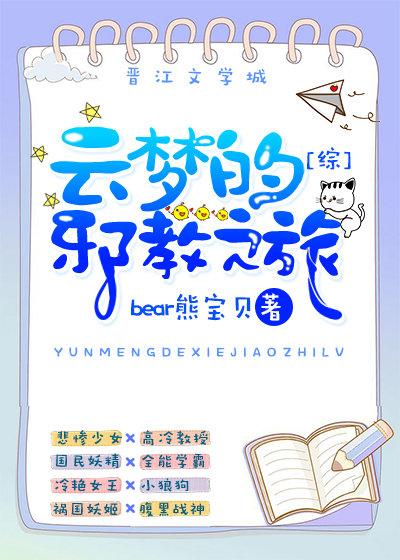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当黑化女主配合攻略 > 第42章(第2页)
第42章(第2页)
他无奈将人捞了起来,微微失笑,鬼修挂在他的身上,眼底蕴着水意,只听她直白而又大胆的对他说:“上面的,今晚你都与我试试。”
行人拥挤,玄已忙伸手去捂她的嘴,被鬼修调皮的叼住一根手指,舌尖贴着指腹的软肉扫了过去,就像那话本里的寡妇一样。
玄已的手指蜷缩了一下,另一只揽着鬼修腰的手不自觉跟着拢紧。
宽大衣袍之下一温一冰的身体不期然紧靠,身后不知是谁推搡了一下,佛子身子前倾,鬼修被他一撞,修长的双腿被迫分出空间。
这个动作,鬼修很难站稳,只能也勾环住他,叼着的手指也咬的越紧。
灼人的热度不知是谁先传了谁,烫的仿佛连空气都烧灼起来,僧人的呼吸不由紧促,衣物靠近的地方隐隐呈现侵略姿势态。
烫人的手忙提着鬼修的腰托举了一下,想借着空隙退开他的身体。
不想鬼修的身体兀得颤栗了一下,提起的身子一软一沉,直接将他勾住,微妙的姿势和触感,两个人具是清晰的感受到了。
鬼修终于安静下来,僧人艰难呼出口气,打算等平复一些离开,没想到,下一刻鬼修低低笑了一声,竟然隔着衣料将手放了下去,被僧人眼疾手快按住,他压抑着粗息,如玉的颈侧因忍耐浮现淡青色的血管。
她真是他的劫。
僧人心头无奈。
经过他们身边的人没能听到他们的对话,反被他们之间的亲昵弄得有些不好意思,甚至刻意忽略掉僧人身上的僧衣,只叹郎情妾意好不般配,纷纷甜着笑意送去祝福的眼神。
可惜,这日最后,画本上的动作到底没有学成,玄已又替她收了许多野魂回来,多到阎心差点以为他是去了鬼蜮打劫。
她看着僧人沾着水汽的僧袍,胸腔没了昨日的满撞,一种没由来的失控和焦躁笼罩在她的心头,那种情绪一下子冲撞四散根本无法抓住,也无法追溯,理智告诉她应该立马摧毁掉面前的人,不然会发生什么令她无法接受的事情,但她就那样看着满屋的蓝色磷火站了许久,什么也没有做,直到僧人将野魂炼化送进她的身体,她才重新有了动作。
她将狗链的机关一一打开,嘴罩、缠捆手脚的链子、钉进脊骨的软钉……
她居高临下一手牵着狗链,一脚踩在他的身上,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重新抓住一些东西。
僧人本可以用他的修为制止发生的一切,阎心也从未有那么一次迫切的希望他反抗自己,但最后,僧人神情温和,依旧好脾气的接受着她对他做的一切,甚至烂好心的在旁助她将野魂炼化。
有了两日的魂补,阎心的修为得到了不少的修复,身体不再像是个漏风的破麻袋,终于可以自行吸收一些鬼气。
此刻,阎心心底像是被人割了一块,半点不比剔骨的时候好受一些,她看着僧人沉静的身影再无半点侥幸——和尚要从她身边离开。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阴霾密布,风卷着粗沙拍得木质的墙壁沙沙作响,少顷,阎心的眼底已密布血丝,她盯视着僧人,过了今夜,她会让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没有再一次意外了!
--------------------
鬼修:没有再一次意外
佛子:不,你有
猫猫:被锁到虚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审核,你别逼我跪下来求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臣妾真没写不能写的啊,明察啊
生障
=====================
上巳节这夜,城里如往年一般取了宵禁,四起的妖风,吹得看不到尽头的长街上的明灯忽明忽暗,依旧阻挡不了年轻男女出行的步伐。
喧嚣的人声顶天,终是打破天字房里自昨日开始的默契沉寂。
窗子被风吹的半开,月华落地,鬼修坐在高椅之上,还是昨日的那身大红嫁衣,复归的鬼气萦绕,脚边一堆染血挂肉的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