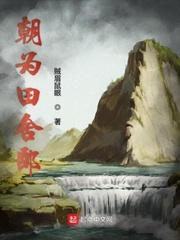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云过天青 > 第九十五章 是她的错(第4页)
第九十五章 是她的错(第4页)
魏师傅笑道,“我才五十,比你那时候年轻。”
“……”
“瓷王”的归属毫无悬念,会场响起响亮却不怎么热络的掌声,景云仿佛能听见各家窑主内心的哀叹,倒也生出些同情来。
越开这家伙讨厌归讨厌,厉害也是真厉害。她当初明明想过不要复仇,不要和他斗,怎么后来还是犯糊涂了呢?
要和他这样的人斗,就得比他更狠、更无情才是。
这个念头刚在她脑中攒聚,会场里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叛徒就该被逐出师门!”
这话着实耳熟,却不是时晨的声音,景云一惊,立刻去搜寻目标,可她还没找到源头,同样的声音就在一瞬间四下响起,继而此起彼伏,像一股汹涌的浪潮,直冲主席台而去。
混乱在一秒内爆发,一大群人毫无征兆地涌上台去,余下的人或惊呼、或哄闹、或向外跑,人头攒动中景云看见了时晨,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显然毫不知情。
如果是时晨的话,他的恨意再大,也只会给越开砸一杯咖啡,而不是时晨的话……
青瓷碎裂的声音如惊雷一般响起,扑上台的人群乌压压的一片,场面彻底失控,越开本是人群中最高的人,此刻却已经没了身影!
景云下意识向台上冲去,像是有人在身后拉她,又像是有人在叫她,但她脑子一片空白,只是拼了命地拨开混乱的人流。
他人呢?
她只有这一个执念,没有理由地奋不顾身。
打斗声越来越近,她清晰地听见骨肉碰撞的声音,自己的后背好像也挨了一下,闷闷的疼,直到她一头扎进最中央,一个陌生男人摔倒在她脚边,她才赫然想起郝一百曾经告诉过她:
——咱们大师兄超级厉害,后踢腿的时候腿长两米好不好!
哦……
她终于亲眼见识到这个画面了。
只是,人还是太多了些,越开的眼角和嘴角都受了伤,握紧的拳头像是被瓷片划破,汩汩地流着血,染在他米色的针织衫上,令她一阵晕眩。
越开没料到会在此刻见到景云,或者说,在这样的混乱中看见她,并非是一件好事。
可一直不都是这样的吗?
他们相遇的时间就不好,喜欢她的时机也不对,想向她坦白却总是错过,但那么多的错误之下,他还是遇到了最好的人。
他墨色的眼瞳被血染红,透出令人生畏的杀气,可恍惚中,景云却看见他笑了一下,然后她被人重重一推,双膝落地,接着是一只锦盒向她砸来。
完了,她如是想,锦盒都是实木做的,她光买了重大疾病险,却没买人身意外险……
一声闷响,是木盒砸到骨头的声音。
木盒碎了,骨头好像也碎了。
但景云毫无痛感,她睁开眼,看见越开挡在她身前,左臂高举,像一棵大树伸出刚硬的枝杈,她又想起一件事来——
他的手臂曾经挨过一棍,骨折后打了两颗钢钉,不能再受伤了。
刺眼的灯光下,凌乱的惊呼中,她觉得自己错了。
阿开属于这里,但越开不属于。
他不应该来的。
是她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