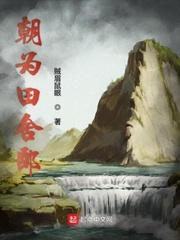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云过天青 > 第九十五章 是她的错(第3页)
第九十五章 是她的错(第3页)
越开默不作声,董小皖讪讪地撇嘴,处男果然是没经验啊。
“对了,还有一件事。”董小皖又道,“明总最近私下联络了几位董事,按说董事长上次已经失败了,他为什么还要再试一次?”
“越明夏这个人比他父亲厉害多了,明的暗的,白的黑的,他都干得出来。”越开捏了捏眉心,“你先回去看看他究竟要干嘛,这边比赛一结束,我回去就是董事会会议了。”
董小皖应承完,忍不住还要唠叨几句,“这个节骨眼,您就不该来的……还有,现在龙家窑的人都不搭理您,我要是一走,可就剩您一个人了,斗瓷那天会不会又有人找茬啊?”
“砸臭鸡蛋、丢菜叶吗?”越开笑了一下,“可我上次被砸的时候,你在场也没什么用啊。”
“唔……”董小皖摸摸眉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但我好歹帮您洗衣服了啊。”
越开嫌弃地看了他一眼,“我发现你最近胆子大了,话也多了,再待下去我可能会忍不住把你开了。”
董小皖委屈地扁了扁嘴,他承认跟老板来天泉镇后,自己的胆子是肥了点,因为老板在这里和在越氏天工完全不一样,他自然有些飘飘然,但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啊!
为此,董·狗头军师·小皖最后一次冒死上谏,“开总,那山的事您要么下狠手,要么和景小姐直接谈,否则人财两失啊!”
越开起身关门,直接把董小皖轰了出去。
房门关上,他才叹了口气,人财两失?他现在还可能人财两得吗?自从来了瓷艺协会,景云就对他视而不见,前几天鹿萱约自己谈事,他们在镇上的饭店撞了个正着,可小狐狸直接从他面前走过,没有斗嘴,也没有冷眼,甚至连余光都没给他一眼。
那天董小皖说,女人不吃醋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在乎了。
越开想,如果他只是阿开,如果一切回到当初,就那样陪着她待在龙家窑,会比现在幸福很多吧。
但是,他的人生根本经不起如果。
***
半个月后,瓷艺大会的最后一天,也是比赛的重头戏——斗瓷。
尽管龙家窑的人对越开不满,但斗瓷还是得来,毕竟捧的是自家场子。如今没了龙千峰,郝一百自然没有头排待遇,只能和景云他们一道坐在会场中央。
斗瓷的流程和以前一样,每七个窑口分为一组,逐一上台比拼作品。龙家窑今年又是压轴,而越开五天前就已经开窑,结果毫无悬念,所以龙洺在座位上打起盹来,只让他们最后叫他一声。
郝一百坐在景云身旁,垂头丧气的,和去年判若两人,景凿墙难得大方,给他递了一块巧克力。郝一百接过来没吃,只在两手间来回摆弄,“你问过他吗?”他含糊不清地说,“当初为什么要走?”
“问过。”景云回他,“出于他的立场和他的目标,舍弃龙家窑是必然的事。”这些天她一直在想鹿萱的话,隐隐有些抽丝剥茧的释然。
郝一百沉默了良久,又问:“那你还恨他吗?”
景云不置可否,只是自嘲地笑了一下,“恨一个人是很痛苦的,用恨来折磨自己,我觉得有点不划算。而且好的心理医生都在私人诊所,医保可用不了。”
“……”郝一百一脸黑线地看向她,她却淡淡地说:“我也好,你也好,我们大家都应该接受一个现实,阿开已经是过去式,不会再有了。”
会场内人多口杂,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一刻也没停过,景云在这片嘈杂声中听见郝一百在低声啜泣,一声隔一声,小心翼翼的。
她仰头看向天花板,使劲眨了眨眼,这会场盖得可真豪华,龙家窑以前没少捐钱吧,不过龙家窑的钱也是阿开赚的……她一时思绪纷乱,费了好大劲才重新凝神。
魏师傅因为有事,来得晚了一些,景云腾出自己的位置让给他,魏师傅坚持不要,两人推搡了几轮,引得后排的人有些抱怨。魏师傅不好意思挡住别人,只得先坐下。景云站在过道上,环视了一圈,“今年来的人好像比去年多,是不是鹿大师以为自己要赢,请帖发早了啊?”
“还有不少生面孔呢。”魏师傅附和了一句,“我都没在镇上见过。”
转眼比赛就到了最后一组,越开端着锦盒与同组的六人一起上台。景云方才说得豁达,这会儿目光还是死死地被越开牵着走,盯着他高大挺拔的身影,盯着他宁静淡泊的眉眼,盯着他骨节分明的手腕……
没出息!
她在心里啐了自己一句,抬手去推打瞌睡的龙洺,因为心情复杂,一时下手重了些,直接把小洺爷的脑袋打到郝一百的脑袋上,两个脑袋咚地一撞,一个不哭了,另一个也不睡了。
台上的越开已经打开锦盒,端出他烧制的青瓷觚,青翠欲滴的釉面在明亮的灯光下折射出炫目的光芒,越开站在那光芒下,就代表龙家窑又赢了。
龙洺揉着额角,不甘心地问魏师傅:“我要学多久才能烧成他那样啊?”
魏师傅倒也坦白,“听说越开九岁学制瓷,学了二十年,换成你的话……得三十年吧?”
“那不是和您现在一个年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