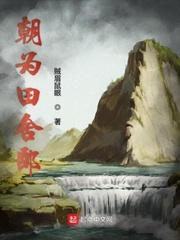墨澜小说>景云阕 > 第121章(第1页)
第121章(第1页)
轻微的触碰混合着旁边小猞猁的骚动,将我搅得坐立难安,我不知怎地就抽回了手臂,对阿姊匆匆说了一句,“我去更衣”,便落荒而逃。
一路狂奔,直到东宫的马场才终于停下脚步,我撑着身子,喘着粗气,贪婪地呼吸着这一处开阔视野中的空气。
“孺人!”我听见阿鸾的声音越来越近,转头看去,她竟抱着那只小猞猁。
“孺人可要抱着它?”
“不要!你来抱着就好。”
无数回忆,关于邙山的回忆、关于凝雨的回忆、关于从敏的回忆,又一次排山倒海地劈来。
我没有想过要忘却,我只是在毫无准备的时候,承受不了那样鲜活的记忆。
有这样一个雪白的小猞猁在身边,我也许回永远锁在过去的梦魇中。
“孺人,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去吧。”阿鸾轻声说道。
一刻、两刻……深秋的冷意渐渐袭满全身,马场旁传来轻微的粪味,等了许久,我淡淡回她:“好。”
返回宴席的路上,我刻意挑了一条林木葱茏的小路,只想将自己埋在一片安静中更久一些。
可是天不遂人愿,偏偏隔着几步就听见一男一女的声音,想来也是离席而来。
“他算什么?一个奴婢生的儿子,你好歹也是梁王的嫡长子,唤他阿兄,不觉得丢面子吗?”
小娘子的声音娇娜又凌厉,我听出了是李裹儿。
“可你刚才……我还以为你在向他示好。”武崇训在旁说道。
“示好?呵,不过是他今日婚宴,做个样子给阿耶看罢了,他也配让我去示好?”
声音不大不小,竟也毫不避讳,果然如我所料,她只是想要讨好父亲,完全没把庶出的兄长放在眼里。
我此刻实在无心顾及,抬手向阿鸾示意,转身想要离开。
还未踏出半步,就见李隆基站在我的身后,他抬起食指置于唇上,一半的脸庞藏在阴影中,悲喜难测,漆黑的瞳仁格外灼亮。
也不知他在这里待了多久,究竟是在我之前还是之后。
我轻轻点头,与他并肩远离了此处。
“三郎”,直到走到空旷的廊间,我压抑着心口的重重忧虑,才开口道,“刚才安乐郡主的话……”
“那是东宫的家事,与我无关,也与父亲无关。”他利落地打断我的话。
我本想言谢,却恍然觉得自己和东宫各行其是,早就没有什么立场了。
阿鸾依旧抱着雪白的猞猁,和眼前李隆基幽深的黑瞳相映成趣。
我突然有了主意。
“三郎,你可还记得你阿娘曾养过一直雪白的猞猁?邙山游猎时,因为救你阿娘而惨死。”
李隆基的眉间闪过一丝警觉,转而镇定答道:“记得的,韦姨。”
“这是太子殿下寻来的猞猁,与从前的那只几乎一模一样。你也知道我往来掖庭与相王府,恐怕无暇照料,不如交由临淄王妃,你得空时也方便常去看看。”
“太子殿下的赏赐……”李隆基犹豫道,“我不敢私自领受。”
“你若有心,留着便是,我自然会想办法同太子妃解释。”
李隆基的黑瞳闪着狐疑而戒备的寒光,他紧紧地盯着我,过了许久许久,才展开眉眼,笑着回道:“那就多谢韦姨。”
我终于松下心来,长吁一笑,“那你为它起个名字吧。”
“我记得……从前的那只叫凝雨,‘凝雨’乃沈休文‘独有凝雨姿,贞婉而无殉’这句诗中对雪的雅称”,李隆基低头思索着,“本朝凤阁舍人张说亦有一句,‘欲验丰年象,飘摇仙藻来’,可堪相较,不如就叫它‘仙藻’吧。”
雪白的毛发和漆黑的眼瞳,在我的两边。倏忽之间,仙藻和李隆基、凝雨和窦从敏,匆匆移到了一处,铺散开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