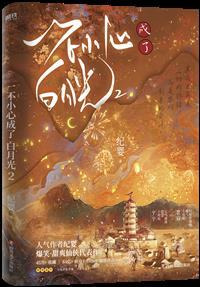墨澜小说>周颖周天赐 > 第2章(第2页)
第2章(第2页)
毕竟,那是我妈。
我甚至动了要举报电子厂用童工的念头,可之前认识那个线长告诉我,我不能这么做,否则就是砸了其他人的饭碗。
我忍着,每个月白打工。
别人在食堂想吃什么吃什么的时候,我跟阿姨为了二两米饭争的面红耳赤,最后还是线长出面,阿姨才原谅我。
别人在休息时间出去玩、花天酒地,我只能求着线长再给我安排任务,我想多挣点钱早点离开这里。
我没日没夜的工作,本来5。0的视力在夜以继日的插零件下,也得眯着眼看远处的东西。
可这些我所有的辛苦,在我妈嘴里只是一句轻飘飘的——
「管她干什么?她在厂里吃香的喝辣的,指不定过的比咱俩这吃糠咽菜好的多呢!实在是人家嫌我笨手笨脚不要我,要不然啊,我也跟她当同事去!」
……
这都无所谓,因为我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严寒虽然总是漫长且残酷的,但终究会结束。
我妈风雨无阻地来拿了两年的工资,我也就干了整整两年。
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她除了钱,还带走了我。
我坐在公共自行车的后座,仰直了身子不想碰到她。
我厌恶她,打心底厌恶,不想跟她有任何接触。
她蹉跎了我的时间。
如果不是我心理强大,早在她的一次次折磨中黯然离世了。
我上过学,我最爱看的是三毛文学,我要跟她一样,也做一个坚强明媚的人。
我不能被现实压垮,不能被妈妈压垮。
否则在我死后,这些都会变成我妈对我的几句轻描淡写的讽刺。
拿着这二年我、我爸和她自己的工资,和从舅舅那好说歹说借出来五千块钱,她总算还完了14万的网贷。
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但也不好。
好是因为她不再欠钱了,也不用担心有要债的随时会轰炸她的电话和短信。
坏的是,还完钱以后,我们一家现在更一贫如洗了。
她多喝了二两,半梦半醒间,总算答应我可以让我重新上学了。
我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就扯着她去给我注销了休学。
坐进教室里的时候,我还觉得恍然如梦。
明明前几天我还在电子厂插零件,现在面前的零件又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文字,这是幻觉吗?
不是。
我想,这是上天有眼。
休学了两年,我是跟着最新一届的高一一起考大学的,因为荒废了两年,我很难跟上最新的内容,但这些都不怕,我可以咬牙坚持下来了。
我要离开这里,永远离开。
我在苦哈哈的百天备战高考的那段时间,周天赐早在我打工那年就考到了本省的一所二本院校,现在他应该读大二了。
说来可笑,当时他的升学宴我还去过。
我灰头土脸的穿着工装坐在下面,迎接着不同人的打量,还有他同学鄙夷的眼神。
我妈打扮得花枝招展,活像个蓝孔雀。
她不顾我们的阻拦,在自己负债累累的前提下,打肿脸充胖子,拿着我半个月的工资给他包了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