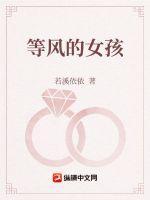墨澜小说>楚楚风云 > 第三十一章(第2页)
第三十一章(第2页)
是传染科病房。
杨小江顿了顿,说:“毒贩被制伏前还在注射海。洛。因,扎破手臂流了血,林琅把他压在地上上手铐的时候,他用带血的针头……扎穿了林琅的手掌。”
徐楚死盯着自己的脚尖,咬住嘴唇。她不小心扯下一片死皮,血腥气浮上嘴边。
“那人得了什么病?”
她忽然很烦这个磨叽警察。
给个痛快吧。
“艾滋。”
徐楚全身一寒。
她料定自己会被结果螫痛,忍不住还是要碰。
果然,给螫了。
她抬眼,望进杨小江厚厚的眼镜片,深深点头。
那点头全是六神无主之人所特有的乖顺。
“……”
徐楚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的理智、逻辑与语言统统在这一刻阵亡。
“你放心,我们送医还算及时,在血液感染的两小时内给林琅吃了阻断药,刚才给他抽了血做初筛,结果明天会出来。”
“他,他进医院后一直昏迷着吗?”
她一瞬间想到很多东西。
缉毒,无名者,遗体告别仪式,还有死亡。
“中途醒过一阵,但很虚弱,林琅左手手掌缝了六针,腿上也有刀口伤,所以说不出什么完整的话。但他……”
杨小江略有迟疑,“一直在重复两个字。你叫徐楚,对吧?”
“……嗯。”
杨小江发觉此时和徐楚沟通是无效的。
这女人只会呆呆地点头,应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行,那你陪陪他吧,有什么事就找护士,楼道里也有我们执勤的同事,你们很安全。”
“嗯。”
等病房门被掩上,徐楚才把包扔到地上,靠着墙壁哭了起来。
两小时前她还在想着他意。淫。
而他那时昏迷着被抬进医院。
徐楚坐到床边的椅子上,隔着眼泪的薄膜,看清了林琅被纱布包得厚如蚕茧的手掌心。
几根手指裸露在外,方正的指甲盖上凝着血痂。
那只用来夹烟的,捺燃打火机的,牵起她手腕的手,此刻无力仰放着,一动不动。
腕骨处的黑皮筋没有了,取而代之是写他名字和床号的黄色腕带。
不过三天,许多事就变了。
林琅睡得很熟,就像那天做完胃镜一样不省人事,陷入死亡般透彻的睡眠。
但现在的她已经不舍得再摆弄他了。
窗外夜幕低垂,屋外走廊静悄悄,屋里有仪器规律而冰冷的滴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