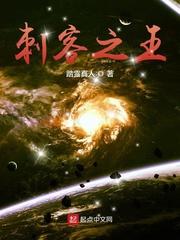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穿书后踹掉夫君 > 闺中对(第1页)
闺中对(第1页)
红烛顶端,焰苗飘摇,暖光满溢。
四四方方的偌大寝殿,由内至外被婢女清洁过一遍,看着还干净。
只是这些木床和架子一类的家具,虽装饰着皇家的华贵纹饰,望上去却格外陈旧。
一眼便知,是多年未曾使用过的,那种落寞的残旧。大概整个房间,也多年没有走进过半个人影了。
贺子衿一路扣着秦鉴澜的腕子,沉默不语,桃花眸中却闪动着道不明的神色,让她看不明白,也就不敢挣开男人有力的手掌。
走近寝殿,有婢女出门相迎,贺子衿简单地说了句这是自己先前住过的地方,两人便进了门。
一跨过高高的木槛,他像是刚回过神来,这才松开了手。
秦鉴澜坐在木桌旁,拈起婢女早先盛在银碟中的深色浆果,往口中递去。
贺子衿立在窗前,手按在窗框上,不知在想什么。两人从回到这个房间开始,就保持着这样的距离。
“贺子衿,”她拇指和食指间还夹着一颗浆果,终于忍不住开口,忧心忡忡地问,“道伦梯布怎么能认定,你就一定看得懂,连他这种占星师都看不懂的东西?”
贺子衿一怔,竟是勾起一个浅笑:“侠女进步了。我还以为,你会质问我,是不是就这样看着他去送死呢。”
简单的两句话,却隐约藏着一丝落寞。他似乎还在期待着见到,那个有时也很冲动的,在脑海中幻想话本里江湖豪情的女人。
秦鉴澜从喉咙深处哼了一声,心想,他是否有点入戏太深,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他自己了。
若是初见时的贺子衿,生存至上,自然是会拒绝道伦梯布的。她再去问他为什么不帮,岂不是既无法说动他去帮助道伦梯布,又容易让他心生反感,对她自己不利么?
这种双输的问题,她才不要问。
果然,女人只要摆脱多余的情感,智商就会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如今她暗自劝说自己,不能全然信他;可又因为暂时难以离开他,只有小心谨慎,还不能激怒他,要维持现状而已。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贺子衿恢复了平常神色,倚着花窗继续说,“你可清楚,道伦梯布的家人,是靠什么认出占星秘卷上的内容的?”
“是哦,”想到干羊皮上横七竖八的墨迹,秦鉴澜一阵头疼,“莫非他们有特殊的写作技巧?”
贺子衿听不懂她玩的现代梗,只是转过身来,目光停留在百无聊赖地拨弄着浆果的女人身上:“西纳尔氏的占星师家族,与大君的雄狮家族、萨仁的海东青家族一样,都是在宿州生活了数百年的大家族。但西纳尔的族人中,只有那位写下占星秘卷的先祖的直系后裔,才能获知解析羊皮卷文字的技巧。因为那种东西是世代相传的,而知识到了道伦梯布这一代,不仅佚失颇多,况且余下的羊皮卷也不知所踪了。”
“既然如此,”她摩挲着指间的深红浆果,似是不经意地问,“道伦梯布和你,其实有血缘关系?”
他自己说的嘛,只有西纳尔家的后人,才能获知解析的技巧。
几米开外,贺子衿望着秦鉴澜。
女子没换下朴素的灰色外衣,白皙的肌肤水灵灵的。剪秋瞳半阖,耳垂晃荡的一抹深碧色,衬得她唇红颊白,美得摄人心魄,美得……没有温度。
那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大婚当夜,他揭开红缎盖头,见到的第一眼。
那时的秦鉴澜,双手交叠放在膝头,矜持地抿着艳红的薄唇,莹白的侧脸散发出乖巧而呆滞的气息。毫无温度,宛若提线木偶。但那时的贺子衿,抱着互不打扰的心愿,故意带着浑身酒气回到卧房。本就不是你情我愿的事,他见此情形,也没多想,撒开手就倒在了床上,睡得昏天黑地。
秦鉴澜也就和衣而卧。洞房花烛夜,两人却一晚无话,正是相安无事。
可是后来,狭窄的车厢内,奔腾的马背上,镇北关的溪边,皂角树下……那些辰光,叫他如何不怀念。
“喂?”那头的女子,把浆果掷回碟中,挑起柳眉,“你别说到一半嘛。”
贺子衿闻言,也就压下一头的心思,正色道:“我原名忙兀·□□,小时候跟着额吉,在靠近镇北关的地方生活。宿州话的额吉,就是都城话里阿妈的意思。我额吉,就是西纳尔家的人,道伦梯布父亲的妹妹。”
“那你说看不懂,岂不是在糊弄他?”秦鉴澜的双手托住下颌,“那点羊皮卷,讲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数百年来,历代大君统治伊始,都会从宝箱中取出一张羊皮卷,”贺子衿抬了下手臂,权当舒展身体,眉中依稀有一点愁云,“西纳尔家的占星师,一代代服侍着大君,同时凭借前辈的教导,试图译出这些文字。当然,大部分时候辨认出来的,也是模糊的诗句、谶歌,不可能有大白话,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君,他在位期间会发生什么事。”
他顿了顿,继续为秦鉴澜揭开隐秘往事:“十三年前,大君战败,逼问道伦梯布的父亲,自己那张羊皮卷上到底写了什么,却没有得到回答。一怒之下,大君降罪于占星师,几乎将那一脉的族人赶尽杀绝,只留下道伦梯布一人。但是,额吉确实没教过我几句,那些羊皮卷,我也真的看不懂。”
这又让他如何开口呢?模糊的记忆深处,夕阳落下的无边原野,女人柔软的掌心落在发顶,那天教会他的一个词:命运。
那是西纳尔家的命运,也是额吉执意带他远走镇北关的契机。
人与事,早就离他很远了。凝结在贺子衿心底,成为一处暗色的沉痂。
那边的秦鉴澜,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并未了然玄衣男人脑海里的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