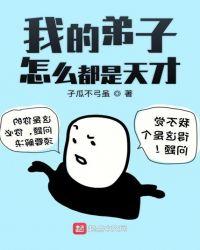墨澜小说>我不为妻 > 第 4 章(第2页)
第 4 章(第2页)
不等沈兰宜再描补,谭清让便转而道:“你说的,确有几分道理。只不过母亲这几年接连病了许久,也是越来越听不得劝了。”
言外之意,便是父母之命,他也没有办法。
沈兰宜当然知道她的婆母许氏有多难缠。因为往后数年,许氏抱病的这些日子,几个儿媳里,数她伺候得最多。
她咬了咬下唇,没再说话,扭身抱起自己的枕头,趿拉起鞋子便要下床。
谭清让皱眉,拉住她露在寝衣外的一节腕子,道:“要做什么?”
又是手腕。沈兰宜一个激灵,被雷劈了似的猛甩开他的钳制。
她像是也被自己吓到了,迅速趿好鞋子站起身,垂着眼帘道:“床榻狭小,我就不挤三郎了,去找珍珠和珊瑚她们凑活一宿。”
前脚说的还是妾,后面见她确实抵触,便改口说是通房。可见此事并非毫无转圜余地。
然而前世做了他十多年的正妻都没有孩子,今生大概也是一样的,虽然沈兰宜此时甚至有点为这件事而庆幸,但是她也清楚的知道,莺莺燕燕进门也将是阻挠不了的事情。
所以,她既不想拦,也不想白吃这个亏。
小孩儿过家家都知道以物换物,她就是要让谭清让知道,她受了这个委屈,才有从他这里图点什么的机会。
“赌什么气?”谭清让话音无奈,“谭家规矩分明,再多女人也越不过你这个正妻去,别担心。”
此时的他与沈兰宜成婚也不过三四载,珍珠未被全然蹉跎成鱼目,两人之间还没有那么多隔阂,他也就愿意哄上两句。
沈兰宜收到了他的态度,却还是没停步,她站在几步开外,欲言又止地看了谭清让一眼。
她没管谭清让有些复杂的眼神,转过身,哒哒地走了。
——
大半夜里,珍珠和珊瑚被自家少夫人的突然出现吓了个够呛。
不过不必和谭清让同床共枕,沈兰宜的心情倒是自在了许多。
从馆驿到城门还有一段不近的路要赶。翌日一早,卯时不到,一行人便动身了。
谭清让带去外任的这些人里,大半是谭家的家生子,阔别家乡和家人许久,越到这个时候,便越是归心似箭,马车轱辘都恨不得不着地了。
今早,潭清让倒是给足了姿态,又是主动来迎沈兰宜,又是搀她先上马车。虽说只是在外人面前做戏抬轿,但总归不是坏事。
试探到了他的态度,沈兰宜心里渐渐便有了盘算。
无论如何,此时他对她这个妻子的态度还是满意的,权衡之上,也乐于往她这边添加筹码。
她能把握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就连这一点微妙的态度都不能放过。
马车行过北山,又颠簸半里进了城门,穿过五六条长巷,赫然便是一片连绵的府宅。
京城地价高昂,居大不易,这边的府宅却都占地宽广,连门口一对对的石狮子都俨然更有威严。
谭府自然也不例外,门楣高挑,漆金的牌匾据说还是前朝某位大家赠与那时谭家家主的物件。
大敞的楠木门边,有两个小厮正垂手侍立在主人家身侧,神色恭谨。
吱呀——顺着石板路上的车辙印,马车停了下来。
驾车的车夫技术很好,车厢并没有剧烈地摇晃,然而沈兰宜却还是感觉自己的心咯噔一下,跳漏了一拍。
她就这么,回到了多年前的谭府。
潭清让察觉到她过于明显的紧张,轻笑了笑,安抚性地拍拍她搁在膝头的手背。
沈兰宜尽量没有瑟缩,她沉下肩、昂起头,跟在自己的丈夫身后,前后脚下了马车。
一抬眼,她便见到了许多张熟悉的面孔。
打头的是谭清让的堂兄、二房的长子谭清成,同他的妻子陆思慧。旁边的另一对,则是谭清让的亲弟弟、大房的谭清文同他的妻子金嘉儿。
论起来,陆氏和金氏,一个是沈兰宜的大嫂,一个是她的弟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