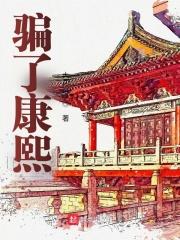墨澜小说>家养小首辅 > 第230章 第230章(第3页)
第230章 第230章(第3页)
老祠堂里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就怕损了什么线索。
此时赵氏所住的那间屋里,聚了许多人。
薛金泉、薛俊才,还有几个薛氏一族的族人都在,薛庭儴也来了,还带来了招儿。招儿有些怕,但实在好奇,又不放心薛庭儴一个人来,便跟着一同来了。
屋子正中用两张条凳架起一块门板,赵氏的尸身便放在上面。
“其实自缢还是他缢,很容易分辨出。自缢,人体的重量全部施加在颈上,是以下颚,也就是这里,作为承重点,所以於痕应该是倒八字,颈骨大多数会断掉。而他缢——”
怕众人听不明白,老仵作叫来自己的儿子做示范。他儿子半蹲着,他则拿了一条绳索,从后面环绕在其颈子上,并缓缓收紧那条绳索。
“他缢的施力范围是四周,也就是圆形或者半圆形的於痕,且位置该是在颈部中央。”
老仵作丢掉手里的绳索,来到赵氏尸体前,将其颈子上的痕迹露出。
“你们看死者的颈部,有两种深浅不一的於痕。一种为一字型,一种却是倒八字。再看其手骨,曲如鹰爪,指甲上也有痕迹,似乎挠伤了什么人,所以结果显而易见。”
招儿忍不住插了一句:“也就说,有人勒死了她,又将之悬挂在房梁上,佯装是自缢而死?”
老仵作见其打扮,又是站在薛庭儴身边,也能猜出其身份,便道:“夫人所言不错,正是如此。”
薛庭儴面露深思,薛家的几个后生已经则群情激奋起来,薛俊才则是来到赵氏身边,双手发抖地跪下了。
也许之前他刻意为薛庭儴开脱,是为了薛氏一族,他也知晓这事怪不上薛庭儴,可现在这种结果反而让他松了口气。
似乎赵氏是他缢而亡,就洗脱了她宁死还要害人一把的恶毒,也让身处在其中的他,乃至是薛庭儴,都显得不那么局促和尴尬了。
“去查,挨家挨户的查,重点放在姓郑的身上。”薛金泉道。
“族长,我们这就去。”
……
老仵作父子被人送走了,处在深夜中的余庆村却一下子苏醒过来。
狗叫声、火把的光亮,以及杂乱的脚步声,拉开混乱的序曲。
“这是咋了?”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响起一个老妇人的沙哑声。
“谁知道咋了,可能是谁家丢了东西。”
说是这么说,郑里正,不,是郑老头,还是披上衣服起来了。起来看动静的,还有他的大儿子郑高峰。
郑家早就分家了,打从郑老头从里正位置上退下来,就分了。是他主动给儿子们分的,理由是不想连累其他儿孙。
站在门前看了会儿,看不出所以然,郑老头便让郑高峰回屋去。
如今的郑高峰一点都没有十年前高大、魁梧的模样,背驼了,腰也佝偻了,头发也早就有了银丝。
是生活的重担,也是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爹,那你也早点回屋睡。”说着,郑高峰就回西厢了。
郑老头独自坐在堂屋的炕上,摸出旱烟锅,又吹燃火折子,点了一锅烟,抽起来。
青白色的烟气在黑暗中蔓延开来,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有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有脚步声响起,似乎来了许多人。
堂屋门一下子被推开了,火把的光亮照亮黑暗的屋子。
“郑老头,把你手和胳膊露出来给大伙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