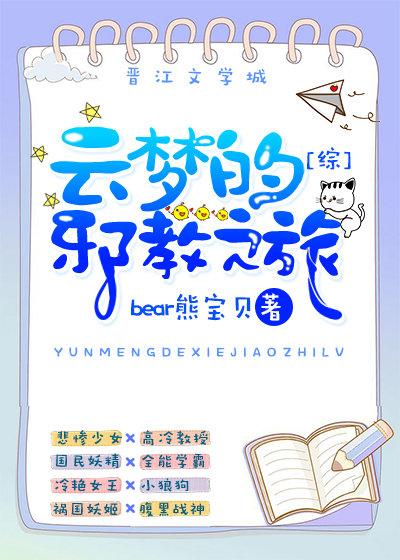墨澜小说>将门三姝 > 第508章(第1页)
第508章(第1页)
宜室长公主正惶惶不安,闻言斥责道:“你不要作怪!这立嗣之争不是我们能掺和的。”
宜室长公主又叹道:“只可惜九皇子是个痴儿,不然我们家还能扶他一把。”
舞阳郡主『露』出了厌恶的神『色』:“扶他干什么?郑惜葭烂泥糊不上墙,他儿子不傻又能聪明到哪儿去!”
宜室长公主皱着眉头道:“你还有脸说别人?你看看你家后院都『乱』成什么样了!先帝一死,我们的优势全没了。现在,辽东郡王和阴城大长公主才站在权势的顶峰。”
“你好好听郑宣行的话。”宜室长公主千叮咛,万嘱咐。
舞阳郡主撇撇嘴,不愿与宜室长公主起冲突:“娘,那您说,最后谁能登位?”
“先帝死,未立太子,朝中一时半会不会追究旁人有没有参与叛『乱』。吴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辽东郡王显然有备而来,这一场风波,还有得闹呢。”宜室长公主看着外头的落日,长长地叹了口气。
嘉梅朱砂写就的劝告书也一字不落地传到了嘉兰的耳中。
嘉菊也跟在她身边,听外头人把都城的消息传来。嘉菊一听,就焦急道:“是不是有人『逼』大姐姐呀?”
嘉兰愣了愣,尔后笑着『摸』了『摸』嘉菊的头:“你怎么会觉得是有人『逼』大姐姐?”
“大姐姐来看过我,她是很温柔的人。”嘉菊嗫嚅道。嘉梅对一个数年未见的她都那么关切温柔,又怎么会自发地写出这样的劝告书,与嘉竹为敌呢?
嘉菊不信。
嘉兰轻叹一声:“不论有没有人『逼』她,在外人眼里,她已经做出了选择。时人不会在乎其中的纠葛和痛苦,他们只能看到表面,便也只会相信表面。”
“不知其中有没有内情,若是没有嘉竹怕是要伤心了。”
正如嘉兰所想的那样,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嘉竹会伤心。嘉竹也的确面有忧『色』,接连打发了好几拨人。等她闲下来得去吴太后跟前装装样子时,她觉得自己脸都要僵了。
嘉竹在福泽宫门口『揉』了『揉』脸,这才走进福泽宫里。
福泽宫还是那副模样,佛龛、香炉、经年不断的木鱼声。
前几次来,吴太后都一言不发,这一次,她终于关切地安慰嘉竹:“竹姐儿啊,你不要为你大姐的事伤心。人啊,各为其主,各有其志。”
“她毕竟也是别人的妻子、母亲,而不仅仅是你的长姐了。便是对你难以顾及,也是在所难免的,你也不要伤心”
吴太后话还没说完,嘉竹就点头打断了她的话:“我知道,我没太伤心。”
她本来也不会打断别人说话的。但是这些车轱辘话她来回听了无数遍,尤其是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希望她最好悲痛欲绝的心态来安慰她的,这让嘉竹实在有些无语。
吴太后一噎,松缓脸『色』道:“不伤心就好。不要像你娘亲,白白为了唉,掷了大把的年华。”吴太后故意没有提是为了谁。
嘉竹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额头:“太后娘娘,这小佛堂里就只有我的人,我们就不要这么虚与委蛇了。”
“你就算来回提我娘亲千百遍,也瞧不见我悲痛欲绝的表情的。不要以为你身陷囫囵,还能运筹帷幄,随意『操』控人心。您的话对有些人兴许管用,对我,还是省了这点力气吧。”
嘉竹说着就站了起来,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悠然自得地喝着秋染给她沏的茶。
“宜安要是知道她百年之后,女儿提起她不见丝毫怀念之『色』,想来也能含笑九泉了。”吴太后讽刺道。
嘉竹啧了一声:“太后娘娘,您这话对付五六年前的我兴许管点用。”嘉竹打量了一下吴太后,道:“既然你老了,就该想到我们也大了。”
吴太后如今极为忌讳别人说她老,立刻就拉下了脸来:“放肆!本宫是你的长辈!”
“父慈子孝,父不慈,子何以孝?为老不尊,虽为老,何以得尊?”嘉竹毫不客气地道。
吴太后神『色』复杂地盯着她:“竹姐儿,你如今不像你娘亲,倒像是蒋嘉兰那个牙尖嘴利的丫头。”
“是吗?”嘉竹唇边有弧度,笑意却十分冷冽:“如果不是你吴家害我蒋府满门,我二姐也不会含辛茹苦地带我长大。我如今也不会像她,说出来的每句话,都能刀刀戳在你的心肺上。”
“啧。我的功力尚浅,若是二姐在这儿,她只会笑盈盈的,让你打落牙往肚里吞,除了夸她好,根本说不出放肆二字来。”嘉竹说着,对嘉兰的想念前所未有地强烈。
“只可惜啊,曾经的将门三姝,如今姐妹决裂,四散天涯。竹姐儿,你身上可也流着楚家的血。”吴太后『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兄弟阋墙,父子相残的血脉。”
这时,半柱香已经燃尽了,嘉竹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看望吴太后的时间已经到了,一刻都不耐烦多待。
“流着谁的血脉有什么关系?吴家也没流着楚家的血,不是更残忍?听说牢里父子兄弟早就恨不得啖对方的血肉,好苟延残喘一日了。”
听到嘉竹的话,吴太后脸『色』一僵。她竟比嘉竹还要沉不住气!
嘉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吴太后,你有空担心我,不如想想你的吴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它,到底已经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