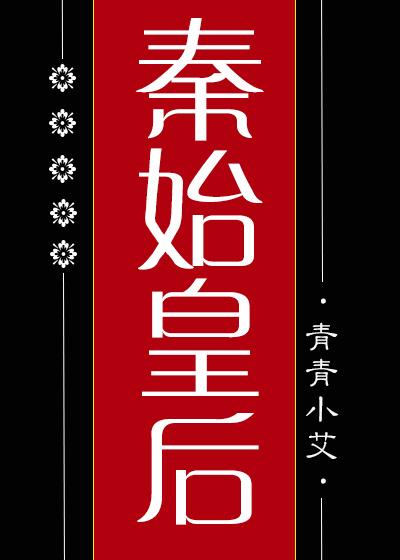墨澜小说>敢问偏执将军悔悟了吗 > 第 95 章 离开北疆(第2页)
第 95 章 离开北疆(第2页)
无忧扬起小手,目送着众人远去,暖暖的春光映在她的身上,她微微颤动着长睫,仿若春日里开的一朵玉兰,极是清丽。
自小陪她长大的人走了,心下却也说不出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瘦削的一抹倩影在城口立了许久。
_
谢实时一路并未停歇,春雪刚化,路上多是难行,一众人马快马加鞭连水也顾不得喝上一口,终是在天黑前穿过了谷口。
待夜幕降临时,方才安营搭灶。
赶路多是带了些干粮,众人就着火堆,将干粮烤热,又喝了几口热水,便也就合衣而睡了。
虽是进了四月天儿,到了夜里风依旧是带些寒气,谢子实被那寒风吹醒。他起身寻着无忧送他的包裹,本想打开拿出两件衣裳,却在手探进包袱时,摸到了那鼓鼓囊囊的一团。
他就着火光将包袱抖开,中间裹着的却是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包还有一封信。
谢子实盘腿坐下,先是将那信拿了起来,在看到那缺笔少画的字迹时,眸子却是不自知的弯起,眼底尽是宠溺。
那信上歪歪扭扭写着:
穷家富路,我知你是赚了些银钱,可京城太远,带着些衣裳银钱,我总归是安心的。
那字写的确实不好看,偏偏在火光中却是生了种力量,谢子实指尖发白,紧紧捏着那封信,好看的唇却是不由自主嗫喏着。
他仰起头望着戈壁上的繁星,心底欲渐起了波澜。
_
大抵是无忧站的太久了,红柳抬手揉了揉眼眶,收起了刚刚被谢子实忽略的一点委屈,走上前轻声说道,“夫人,日头大了,不如咱们先回府?”
无忧被这一声惊回了神,她抬起素手揉了揉脸颊,回身说到,“走吧。”
这两人才一转身,还没行至车却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马声。抬眼瞧去,却见是陈庆,一身玄甲负手勒住了缰绳,许是天热的缘故,本是小麦色的脸上却染上了几丝红。
他翻身下马,阔步来到小姑娘身前,压低着嗓子问道,“大宝走了?”
本是粗枝大条的人,一朝却变得小心翼翼的样儿,倒是惹得小姑娘提起了兴致。
无忧一扫离别的不快,她望着人高马大的陈庆点点头,本想再说点什么,却瞧陈庆只是猛一敲头,嘴上咕哝了两句,便又脚下生风,匆忙的转身要走。
无忧还从未见过这般的陈庆,大哥多的是憨厚沉稳,何时竟成了这般毛躁的性子?
心下生疑,点起脚刚要开口,便见又是一匹骏马驰来。只还未待那马儿停下脚儿,陈庆却如被烧了屁股的猴子,掉头便要跑。
却也没有跑成,还没待翻身上马,便被一对纤臂束住了腰身。
那对纤臂的主人轻轻将头抵在陈庆的肩上,轻呼道,“陈庆!你到底还要去哪里呀?”
“躲得了一时,你还躲得了我一世不成?”
陈庆粗红着脖子,想要去拨开腰间的双臂,却又无从下手般,结结巴巴的对着善雅道,“你是女子,怎可这般”。。。
“啊,这般什么?”善雅顺势环上陈庆的脖子,也顾不得身侧到底有多少人观望,只转过身对着那手足无措的男人笑道,“你倒是说,我怎么了?”
她笑的张扬又好看,不似寻常女子的娇羞,倒是多了几分男儿家的英气。
“你倒是娶了我吧!我从第一眼看见你,便觉着你好看,陈庆,你倒是。。”她嘴上说的极是轻快,而被她环着的男人脸却是红到发紫,仿佛要渗出血来。
陈庆也顾不上旁的忙伸出大掌,似是求救般的对无忧喊到,“忧娘,忧娘,来,你来帮帮大哥。”
而无忧早已是被这一幕惊的睁圆了双眸,她眨了眨眼,侧身对着红柳问道,“那个是大哥和善雅公主?”
红柳亦是被惊的撑圆的下巴,她咽了咽干巴巴的喉咙,有些迟疑,“是。。。。是的吧?”
她不熟悉善雅,就偶有见过几面,还是从无忧被绑时,才知那个英气十足的女子原是突厥公主。
“唔。。。”无忧点点头,那便是了,前些日子宋燎恩曾说过这善雅公主对大哥有意,不成想,二人竟到了这般浓情蜜意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