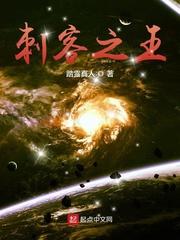墨澜小说>大明英华 > 410章 讨官下(第1页)
410章 讨官下(第1页)
龙椅上,朱常洛颔首,表示认可郑海珠切中肯綮。
座中,有一人却已面带寒霜。
正是新上任的兵部左侍郎,熊廷弼。
郑海珠那一番话,军情、军职、军饷,样样离不开一个「军」字,字字好像在戳他兵部的脸。
楚人熊廷弼,比杨涟还性情耿直、喜欢硬刚。
他才不管对面的妇人,在传闻中收拾掉了他熊廷弼的宿敌姚宗文,更不会因郑海珠的举荐就对其感恩戴德。
屁股坐到了兵部,就不许别个在御前明枪明棒地说他兵部遥控边情有漏洞。
熊廷弼在喉管深处,发出沉重的咳音。
朱常洛看向他:「熊侍郎有话讲?」
熊廷弼道:「臣到任兵部之际,正值杨涟赴任辽东经略之时,吾二人有详谈,皆以为,辽将不可信。那些新旧将门,或许深谙养寇自重之计。郑夫人以为如何?」
郑海珠对熊廷弼要炸毛,意料之中。
换她是兵部侍郎,也会先跳出来,在朱常洛这位大老板面前撇清责任,官场之道而已。
郑海珠于是坦然回应:「熊侍郎的意思是,鹅毛城陷落于张培病故之后,并非因朝廷调度不及时,而是因为,辽将本就会对有些军堡怠于防守或援应,给建奴胜一场,造成虏情又炽的迹象,多问毕尚书的户部要些公帑银子,反正辽饷科里这大半年有储备了?」
「正是。」熊廷弼盯着郑海珠。
无论年纪、资历,还是自负的阅历,甚至一个来自火辣荆楚、一个来自温柔江南的出处,都令熊廷弼此刻的态度,看起来要比郑海珠显得生硬许多。
熊廷弼上一次巡抚辽东时,是万历年间,朱常洛还在做窝囊太子,对此人的能力和官声不熟。
此刻,中年天子心里不免嘀咕,郑师傅,你去蒙古前就与朕唠叨过这个楚党的熊廷弼,说他是文臣里少有的尚武知兵之人,现下你看看这只九头鸟,抬嘴就啄你。
郑海珠却一副「你强任你强,清风拂山岗」的姿态,干脆心平气和地点穿:「新官不理旧官的账,侍郎领本兵之职才几天,今日我说军情延误,也不是冲着侍郎来。此其一,其二,辽东将门根基深厚不假,但嘉靖爷时,朝廷就已有应对,如今李成梁唯一能打的儿子,守在开铁,并未执掌辽沈兵权,抚顺清河一带的参将守备们,几乎已没有李家旧部。至于张承胤、邹储贤、毛文龙等骁将,抚顺一战对老酋下死手,近年又逼得抢不了西边,中外皆知,若朝廷连他们都不信,熊老爷说,该信谁?」
「郑……」
熊廷弼一个「郑」字刚滚到胡茬边,郑海珠就止住他:「我还没说完,其三,熊侍郎的担忧,实则恰恰还是回到我方才说的关窍上,即,朝廷到底知道多少真相?掌握真相后,谋断与决策到底是不是合理?兵贵神速,谋定而动,这两个看起来截然相反的主张,其实就与主战还是主和一样,对错与否,全看情势而已。」
熊廷弼原本面色还要再难看一些,但细品这妇人说的第三点,是知兵之论,且她确实并无与自己唱对台戏的意思,目光中的森然之意,稍稍淡了几分。
朱常洛适时地发话,以最高决策者平易可亲的圆场口吻,对首辅叶向高和次辅周嘉谟笑道:「叶先生,周先生,你们瞧,这两个都在辽东地头干过的人,就算吵嘴,说的都是内行话。不错,朕就爱听这样的争执,不来虚的。呵呵,呵呵……」
天子的一串儿「呵呵」,都察院左光斗和户部毕自严听来没什么反应,始终琢磨何时开始说台词的吏部尚书商周祚,则犹如听到锣音似地,准备登场了。
「陛下,巡按御史不过七品,郑夫人论来是六品,要不就在熊侍郎的
兵部挂个什么衔头,巡按辽东吧?」商周祚说着,又转向左光斗,「总宪,听闻杨经略当初,还举荐过郑夫人为皇子进讲,那不正好,大伙儿在辽东,都能说到一处去。」
左光斗倒不把商周祚看成浙党,对他很客气,和风煦日地附和着笑笑,笑完了却在心里猜测,今日郑氏一定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以至于吏部天官,都在为她铺垫。
果然,天子接过商周祚的话头,问郑海珠:「你敢去兵部领饷么?」
郑海珠起身,一板一眼道:「陛下,臣在崇明有兵部在册的营兵,新近升任游击的许一龙所部,领的就是兵部饷银。即使盛世天子有如海胸襟,即使各位老大人有破格提携美意,不虑一个妇人并无科举功名,就愿授官,我郑氏亦不可再挂兵部的虚职。至于巡按御史,容郑氏斗胆说一句,他们只有弹劾纠察之职,当初圣令遣我去察哈尔,托巡按宣大关外之名,已有些牵强。故而,郑氏今日,以忠君报国之诚,欲开先河,向陛下,向我大明朝堂,求一新职:国务卿。」
此话落地,曹化淳利用站在天子身侧的便利条件,迅速地将众人的面色都扫视一遍。
大明目下能陪着万岁爷作决策的文官,都在这屋子里头了。
首辅叶向高面上,无波无澜。
次辅周嘉谟瞄了一眼叶阁老,很快收回目光。
户部尚书毕自严微微前倾身体,想再确认一下是哪三个字,但又靠回椅子上,一副「我又不是吏部尚书」的自觉认知。